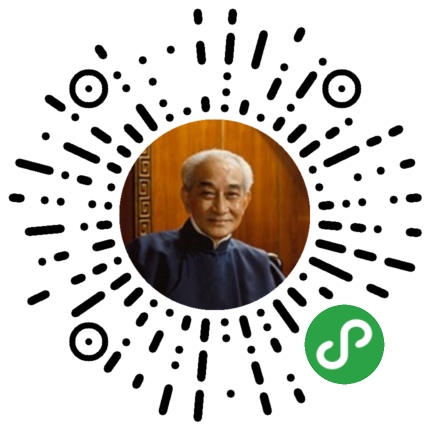「 史料 」周朝進:我知道的(de)南(nán)懷瑾先生
編者::本文原載于樂(yuè)清日報全媒體(2019年6月(yuè)28日。
我知道的(de)南(nán)懷瑾先生
周朝進

記得(de)1988年夏天,我的(de)堂弟(dì)周朝春與我說,他(tā)嶽父林(lín)夢凡先生,有一位旅居美(měi)國的(de)朋友,是樂(yuè)清人(rén)到台灣的(de),最近寄來(lái)很多(duō)書(shū)籍,有關于《易經》《論語》等等。樂(yuè)清有著作等身的(de)這(zhè)樣一位大(dà)學問家不知道是誰?我要去了(le)解一下(xià)。于是,在一個(gè)星期日,由朝春堂弟(dì)陪同,去拜訪林(lín)夢凡先生。
林(lín)夢凡先生原住樂(yuè)清縣城(chéng)太平巷,後随小兒(ér)子同住在樂(yuè)成銀溪李宅坦。住址正是樂(yuè)清傳說中李先峰老宅的(de)後座屋,北(běi)首是李宅大(dà)屋和(hé)洪宅大(dà)屋。夢凡先生住在東首正間。一進門,朝春向林(lín)夢凡先生介紹了(le)我,大(dà)家寒暄了(le)一下(xià),便坐(zuò)下(xià)來(lái),師母就泡茶了(le)。房(fáng)間南(nán)面闆壁上挂著(zhe)一個(gè)鏡框,嵌著(zhe)一幅書(shū)法,是南(nán)懷瑾先生的(de)七律詩。曰:
接著(zhe)林(lín)夢凡先生就談起了(le)南(nán)懷瑾先生。他(tā)說,南(nán)懷瑾先生童年時(shí)在家上過私塾,讀過《三字經》《千家詩》《幼學瓊林(lín)》啓蒙書(shū)和(hé)《四書(shū)五經》等,但算(suàn)術、自然、地理(lǐ)等知識未讀過。他(tā)父親通(tōng)過關系,總算(suàn)把他(tā)送到縣立高(gāo)等小學,插班讀六年級。因他(tā)家在翁垟,當時(shí)交通(tōng)十分(fēn)不便,進縣城(chéng),要麽步行,要麽乘小船,學校又沒有寄宿。他(tā)父親在縣城(chéng)裏找到了(le)我父親(林(lín)占魁先生),讓南(nán)懷瑾借住在我家裏。正好我也(yě)在縣立高(gāo)等小學讀書(shū),兩人(rén)可(kě)作伴。我母親對(duì)南(nán)懷瑾很好,像對(duì)自己的(de)兒(ér)子一樣。我與懷瑾同窗(chuāng)、同吃(chī)、同住,情同手足。南(nán)懷瑾先生在縣小學上了(le)一個(gè)學期,就小學畢業了(le)。後來(lái),他(tā)在家裏又随表兄王世鶴,從宿儒朱味淵先生讀古文,習(xí)詩詞歌(gē)賦等,也(yě)學了(le)一個(gè)假期,而對(duì)味淵先生的(de)教誨終生難忘。接著(zhe)他(tā)在家自修三年,讀了(le)不少書(shū),如《史記》《文選》,還(hái)有唐詩宋詞、小說筆記等等。
爾後,他(tā)14歲在家裏自修。18歲赴杭州,入浙江省國術館學習(xí),20歲畢業,任浙江省學生集中訓練總隊技術教官。1937年七七事變,他(tā)由杭州迳赴四川成都,參賢訪道。22歲創辦“大(dà)小涼山墾殖公司”。23歲于四川成都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教官。24歲于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研究班(第十期)修業。25歲參加袁煥仙先生主持的(de)灌縣靈岩寺禅七。26歲入峨眉山大(dà)坪寺閉關。29歲走康藏參訪密宗上師,爾後,轉杭州,30歲返樂(yuè)清故裏省親。
後來(lái),林(lín)夢凡先生也(yě)赴南(nán)京國民政府下(xià)屬的(de)一部門供文職。1949年,南(nán)懷瑾先生曾勸說林(lín)夢凡先生一起赴台,但林(lín)夢凡先生一來(lái)留戀故土和(hé)家庭,二來(lái)自覺得(de)僅隻是國民政府下(xià)屬一小文職員(yuán),沒有拿過槍、殺過人(rén),新政府不會爲難他(tā),便選擇留在了(le)樂(yuè)清。後來(lái)就像大(dà)多(duō)數曾經任過僞職人(rén)一樣,不幸遭受了(le)數次的(de)清算(suàn)。1949年南(nán)懷瑾先生32歲隻身赴台。從此,兩岸阻絕,杳無音(yīn)信。
1985年,因受台灣政界“十信案”嫌疑,南(nán)懷瑾先生于7月(yuè)4日赴美(měi),離開居住了(le)36年的(de)台灣。到美(měi)國,在稍事安定後,他(tā)立即著(zhe)手聯系國内的(de)親朋好友,并派學生來(lái)國内尋訪。據說,1987年秋,南(nán)懷瑾先生派朱文光(guāng)博士來(lái)國内辦事,交代他(tā)到樂(yuè)清縣城(chéng)太平巷尋訪林(lín)夢凡先生。因太平巷附近的(de)老鄰居多(duō)有變遷,而且林(lín)夢凡先生在家裏,人(rén)們隻知道其小名,不知道他(tā)的(de)學名。尋訪者無果而回。後來(lái),南(nán)懷瑾先生與朱味淵先生公子溫州朱璋(筱戡)先生聯絡上了(le)。于是,朱璋先生特意來(lái)樂(yuè)清聯系上了(le)林(lín)夢凡先生,告知懷瑾先生在美(měi)國的(de)通(tōng)信地址和(hé)電話(huà)号碼。夢凡先生立即給懷瑾先生寫信。1987年5月(yuè),收到了(le)懷瑾先生美(měi)國寄回的(de)信。信是這(zhè)樣寫的(de):
今天突然接到你倆來(lái)信,真如夢中。三四十年間,有關你倆生死存亡,時(shí)在縈懷,我在台北(běi)36年,每逢樂(yuè)清鄉人(rén)即探聽(tīng)兄等消息:據說:極難保險,多(duō)半不在人(rén)間。爲此,頗爲疑念。今知故人(rén)無恙,所有疑雲,渙然冰釋。吾兄能度此浩劫,仍亦天幸矣。我極忙,且将有歐洲法國、比利時(shí)等地之行,但亦随時(shí)轉回此地美(měi)國。一切情形,你可(kě)與朱璋兄連絡或到朱璋兄處可(kě)見我諸事之一斑情況。……
目前無暇與你多(duō)述舊(jiù)情,或随手檢一、二本書(shū)及資料,另郵寄你倆。今先寄你倆美(měi)金旅行支票(piào)一百元,你向銀行問清簽名可(kě)立即兌取。……先作治病費用(yòng)。但須抽一點錢,代我買祭品向令尊堂靈位拜祝,因我實念念不忘令堂之惠愛(ài)深惜也(yě)。照(zhào)片一張,聊當見面。……
從而南(nán)懷瑾先生和(hé)林(lín)夢凡先生失散36年,終于重新取得(de)了(le)聯系,之後兩人(rén)一直保持著(zhe)書(shū)信往來(lái)。懷瑾先生還(hái)不斷地将自著的(de)書(shū)籍寄給夢凡先生,在書(shū)的(de)扉頁均簽上“夢凡吾兄教正”等字。夢凡先生正間裏的(de)竹制書(shū)架上面,擺滿老古文化(huà)事業出版社出版的(de)豎排《原本大(dà)學微言》《論語别裁》《老子他(tā)說》《孟子旁通(tōng)》等著作。
而且,懷瑾先生尊崇古禮,不忘手足情深,每年端午、中秋、歲末年首,都給夢凡先生電彙美(měi)金緻賀節日,有時(shí)忙了(le),就派兒(ér)子南(nán)小舜親自登門将紅包送來(lái),我在夢凡先生家做(zuò)客時(shí)也(yě)遇見兩次,真是難能可(kě)貴。
1988年1月(yuè)懷瑾先生離開華盛頓,回國移居香港。他(tā)在香港通(tōng)訊聯系更便利多(duō)了(le)。1993年,林(lín)夢凡先生夫人(rén)患有風濕病,經常全身疼痛,甚至下(xià)肢浮腫,影(yǐng)響夜間睡(shuì)眠。懷瑾先生得(de)知後,緻信敦促夢凡先生偕夫人(rén)去廈門南(nán)普陀療養。懷瑾先生聯系好方方面面,囑咐他(tā)們倆在南(nán)普陀寺掛褡,治病去廈門大(dà)學附屬醫院診療,一切費用(yòng)開銷由懷瑾先生負責。還(hái)托張定鈞先生先帶給夢凡先生偕夫人(rén)美(měi)金二千元,作爲醫療費用(yòng)。懷瑾先生真是用(yòng)心良苦,精心策劃,足見其對(duì)待同學朋友的(de)一番苦心。
他(tā)給南(nán)普陀寺妙湛長(cháng)老,在南(nán)普陀寺修行的(de)樂(yuè)清籍的(de)誠信、了(le)法法師寫了(le)介紹信:
茲有我之同鄉知友林(lín)夢凡先生、謝蘭女(nǚ)士兩位伉俪,因年邁色身多(duō)病,特請其南(nán)來(lái)就醫,望在南(nán)普陀客房(fáng)較爲長(cháng)住一段時(shí)期,也(yě)算(suàn)是客位性質亦可(kě)。至于叨擾常住之食宿住處等一切有關費用(yòng),請誠、了(le)兩位示知,或轉告宏忍一統由我負責奉上。費神之處,感同身受。
接著(zhe)懷瑾先生又爲夢凡先生去南(nán)普陀,給正在廈門大(dà)學中醫學院進修的(de)宏忍法師,寫了(le)介紹信:
我的(de)童年同學林(lín)夢凡先生、謝蘭女(nǚ)士,因久病,特請其來(lái)南(nán)普陀掛褡治病。望你代表我請中醫學院部内科、針灸科等諸位教授,予以悉心治療。如需住院或使用(yòng)中西藥物(wù)等費用(yòng),統由你代勞辦理(lǐ),費用(yòng)一切,傳真告知我,皆由我負責照(zhào)付。并向諸位教授醫師代我緻意拜托。
實際上,懷瑾先生請來(lái)廈門南(nán)普陀治病,是埋有一伏筆,就是這(zhè)年底,他(tā)應妙湛長(cháng)老之邀,要到廈門南(nán)普陀寺主持“南(nán)禅七日——生命科學與禅修實踐研究”的(de)活動,想在廈門,兩位闊别多(duō)年的(de)老同學、老朋友,能團聚在一起,共叙舊(jiù)情。林(lín)夢凡先生也(yě)與朝春和(hé)我相討(tǎo)過,我說這(zhè)是件很好的(de)事,也(yě)勸說林(lín)夢凡先生早日成行。朝春堂弟(dì)說陪伴他(tā)們去廈門。奈何,夢凡先生是一位十分(fēn)傳統的(de)人(rén),生怕給别人(rén)添麻煩事。就這(zhè)樣,錯失良機,是年底,南(nán)小舜回來(lái)傳信說,參加過這(zhè)次南(nán)普陀寺“禅七”活動,這(zhè)次規模之龐大(dà),竟有七百人(rén)之多(duō),臨時(shí)趕來(lái)旁聽(tīng)的(de)也(yě)有不少。禅堂隻能容下(xià)半數,其餘的(de)一半,隻能坐(zuò)在樓下(xià)講堂,借著(zhe)閉路電視,聽(tīng)先生說話(huà),并觀看禅堂的(de)活動。參加的(de)人(rén),從美(měi)國、法國、香港、加拿大(dà)、台灣分(fēn)道而來(lái),但最多(duō)的(de)仍屬大(dà)陸同胞,也(yě)有從各地寺院來(lái)的(de)老修行及不少老居士。
這(zhè)時(shí),使人(rén)想起唐代詩人(rén)杜甫的(de)《贈衛八處士》詩:“人(rén)生不相見,動如參與商”,“少壯能幾時(shí),鬓發各已蒼”的(de)詩句來(lái)。他(tā)們兩人(rén)是小學同學,分(fēn)别了(le)四十年,經曆了(le)多(duō)少劫難,而今都是白發蒼蒼的(de)老人(rén),他(tā)們的(de)重逢相聚在一起,還(hái)能有幾次?就這(zhè)樣,錯失良機,“明(míng)日隔山嶽,世事兩茫茫”,現在兩位先生都已歸西,但願他(tā)們在天堂相聚,共叙舊(jiù)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