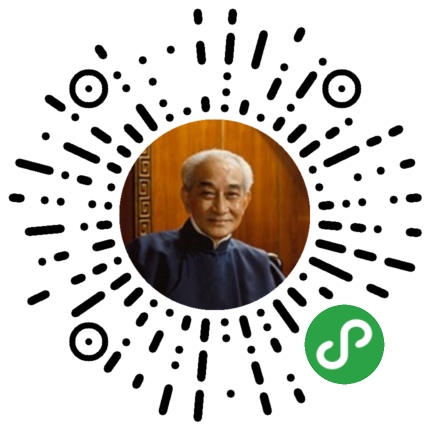南(nán)師史料
王雷泉教授:高(gāo)高(gāo)山頂立 深深海底行 ——南(nán)懷瑾先生文化(huà)史
王雷泉教授:1952年生,上海人(rén),無黨派人(rén)士,複旦大(dà)學哲學學院教授,複旦大(dà)學宗教研究所所長(cháng)、宗教學系主任。中國佛教協會漢語系教材編審委員(yuán)會咨詢委員(yuán)、中國佛教文化(huà)研究所特約研究員(yuán)、中國社會科學院佛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(yuán)、中國佛學院客座教授、閩南(nán)佛學院客座教授。代表作:《摩诃止觀釋譯》《中國文化(huà)辭典·宗教編》《中國思想家傳記彙诠》《中國學術名著提要·宗教卷》《禅與西方思想》《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》宗教卷、《中國佛教的(de)複興》。個(gè)人(rén)研究風格:不尚空談,不作違心之論,力圖以史料和(hé)事實表達對(duì)中國佛教的(de)反省與前瞻。
本文原載于《複旦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一九九六年第三期。
[ 内容提要 ] 南(nán)懷瑾的(de)文化(huà)史觀,源于他(tā)對(duì)人(rén)生苦迫性的(de)否定及超越。從其求道經曆及著述來(lái)看,他(tā)始終堅持佛教傳統的(de)修證道路,以出塵脫俗的(de)第一義谛作爲終極。根據其師袁煥仙“非離真而有妄,實藉妄以诠真”的(de)觀點,真與妄、體與用(yòng)、經與史,皆爲一體二面的(de)統一體。故能圓融無礙地出入經史諸子百家,以孔孟之學的(de)王道德政作爲治事與立身、立國的(de)中心,而以《戰國策》《孫子兵(bīng)法》等作爲權變、應變、撥亂反正的(de)運用(yòng)之學。因此,了(le)生脫死的(de)佛法,必須落實在現實人(rén)生。亦即藥山禅師所謂“高(gāo)高(gāo)山頂立,深深海底行”。無論是出世做(zuò)宗師,還(hái)是入世當英雄,關鍵皆在于把握時(shí)節。南(nán)懷瑾認爲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,進入國運轉盛的(de)新時(shí)期,一切有志者應爲國家民族效力,而不要沉湎于仙佛之道。
南(nán)懷瑾先生的(de)學問規模和(hé)抱負,很難用(yòng)通(tōng)常的(de)學術尺度來(lái)格量。南(nán)先生平時(shí)教育弟(dì)子的(de)理(lǐ)想人(rén)格,扼要的(de)說,就是“敦儒家之品性(孔孟做(zuò)人(rén)處世的(de)方法),做(zuò)道家之工夫,參佛家之理(lǐ)性和(hé)見地。如此才能做(zuò)一個(gè)完整的(de)人(rén),出世成佛,入世則己立立人(rén),而及國家、天下(xià);如此才能爲世必不可(kě)少之人(rén),能爲人(rén)必不及之事,庶幾此生不虛。”[1]而自撰《狂言十二辭》,則以亦莊亦諧的(de)筆調、可(kě)歌(gē)可(kě)泣的(de)心緒,爲世人(rén)呈現出一個(gè)勘破塵世炎涼的(de)獨行者的(de)自畫(huà)像:
以亦仙亦佛之才
處半鬼半人(rén)之世
治不古不今之學
當談玄實用(yòng)之間
具俠義宿儒之行
入無賴學者之林(lín)
挾王霸縱橫之術
居乞士隐淪之位
譽之則尊如菩薩
毀之則貶爲蟊賊
書(shū)空咄咄悲人(rén)我
弭劫無方喚奈何
[2]
“因人(rén)論世”與“因世論人(rén)”
南(nán)懷瑾的(de)文化(huà)史觀,源于他(tā)對(duì)人(rén)生苦迫性的(de)否定及超越。他(tā)常說,人(rén)生數十寒暑,孩童老邁過其半,夜眠衰病過其半,真正昭靈自在,知自己所以爲生者,攢積時(shí)日不過六、七年而已。況在此短暫歲月(yuè)中,既不知生自何處來(lái),更不知死向何處去,煩憂苦樂(yuè),聚擾其心。近如身心性命所自來(lái)者,猶未能識,遑言宇宙天地之奧秘,事物(wù)窮奇之變化(huà),固常自居于惑亂,迷晦無明(míng)而始終于生死之間。如同《易經》最後“未濟”卦所示,人(rén)生是一個(gè)沒有結論的(de)過程,永遠(yuǎn)是有缺憾的(de)。無論是從事出世事業的(de)宗教家和(hé)大(dà)哲學家,或是從事入世事功的(de)偉人(rén),都跳不出生死的(de)自然規律。正當他(tā)曆經青年和(hé)壯年,腦(nǎo)力和(hé)智慧剛好成熟,經驗的(de)累積正達高(gāo)峰的(de)時(shí)候,便像蘋果一樣,紅透熟爛,還(hái)歸虛無。因此,由人(rén)創造的(de)曆史文化(huà),也(yě)就表現爲永遠(yuǎn)是不成熟的(de)。前一代經曆過的(de)一切成敗悲歡,注定了(le)下(xià)一代還(hái)得(de)重演一遍。于是人(rén)類智慧永遠(yuǎn)以二、 三十年的(de)經驗接續下(xià)去。“古今中外,累積幾千年來(lái)的(de)曆史與文化(huà),可(kě)以說都是青年人(rén)扮演主角的(de)成果,中年或老年人(rén)擔任編輯而寫成;它永遠(yuǎn)都很年輕,并且尚未完全成熟。”[3]
這(zhè)種不成熟的(de)人(rén)生和(hé)曆史,在于人(rén)的(de)心理(lǐ)上永遠(yuǎn)處于不滿現實而又不得(de)不适應現實的(de)矛盾之中。人(rén)類的(de)基本問題沒有解決,對(duì)于曆史也(yě)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(de)觀點:若從物(wù)質文明(míng)與人(rén)的(de)現實生活言,曆史不斷地向前推進,必然需要在器物(wù)的(de)進步中更求進步;若從宗教性道德觀念的(de)立場(chǎng)言,則精神文化(huà)又是在“人(rén)心不古”、“世風日下(xià)”的(de)哀歎下(xià)不斷退化(huà)。二十世紀是一個(gè)動蕩的(de)時(shí)代,二十世紀的(de)中國,更是在内憂外患中颠沛困頓。生長(cháng)在東西新舊(jiù)文化(huà)交互排蕩撞擊中的(de)中國人(rén),思想常陷于進退失據的(de)矛盾混亂之中。無論是不滿現實的(de)青少年,還(hái)是歎息“人(rén)心不古”、“世風日下(xià)”的(de)老前輩,究其實都跳不出循環式的(de)曆史悲劇:曆史時(shí)代的(de)途程在不斷地向前推進,而人(rén)類在時(shí)代的(de)輪轉中,卻永遠(yuǎn)不滿現狀[4]。
如何面對(duì)這(zhè)缺陷、不完滿的(de)曆史和(hé)人(rén)生?考諸二千多(duō)年前的(de)聖賢,有“因人(rén)論世”與“因世論人(rén)”兩種角度。孔子著述《春秋》,把遭逢曆史巨變的(de)過錯,責之于當時(shí)身在其位,力足以謀國的(de)“賢者”,此謂“因人(rén)論世”。釋迦的(de)真理(lǐ)則是“因世論人(rén)”,認爲曆史變亂的(de)罪過,是人(rén)類與一切衆生的(de)共同“業力”所造成。當共同“業力”構成大(dà)勢所趨的(de)時(shí)期,猶如轉動速度極快(kuài)的(de)火輪,誰也(yě)無法插手使其停止。老子的(de)“無爲”、“因應”觀點,也(yě)與佛法深悲衆生“定業”難移的(de)觀點相同而立論。[5]
佛家“因世論人(rén)”,以超越世俗的(de)解脫者高(gāo)度,俯視在三世輪回的(de)業輪中,芸芸衆生定業難移,故一切有賴于時(shí)節因緣的(de)成熟,把人(rén)生問題的(de)解決延長(cháng)到無限久遠(yuǎn)的(de)三大(dà)阿僧祇劫。儒家“因人(rén)論世”,則在一期生命中,以天下(xià)興亡、匹夫有責的(de)曆史責任感,縱然是知其不可(kě),也(yě)要勉而爲之。這(zhè)兩種觀點,若以第一義谛與世俗谛體用(yòng)不二的(de)佛家觀點來(lái)看,表現爲“上求菩提、下(xià)化(huà)衆生”的(de)辯證統一,都有其存在的(de)價值和(hé)理(lǐ)由。而具備大(dà)仁大(dà)勇智慧的(de)人(rén)物(wù),所抉擇的(de)人(rén)生道路不外乎兩條:不爲英雄,必爲聖賢。
南(nán)懷瑾将英雄事業稱爲“人(rén)爵”,聖賢事業稱爲“天爵”。[6]即生完成赫赫事功,名揚千古的(de)便是英雄;而聖賢事業,也(yě)許寂寞一生,卻能永遠(yuǎn)賦予人(rén)們以身心的(de)安泰。“英雄能夠征服天下(xià),不能征服自己,聖賢不想去征服天下(xià),而征服了(le)自己;英雄是将自己的(de)煩惱交給别人(rén)去挑起來(lái),聖賢自己挑盡了(le)天下(xià)人(rén)的(de)煩惱。”[7]英雄是世間凡夫的(de)頂點,而在聖賢事業中,則有儒道佛三教的(de)次第展開。聖賢領導了(le)古今中外曆史的(de)趨向,非帝王将相之所能爲。故在《景印〈雍正禦選語錄〉暨〈心燈錄〉序》中,一反常人(rén)将雍正比爲漢景之刻薄的(de)定評,對(duì)其振興禅宗的(de)作爲給以相當的(de)好評:“英明(míng)如雍正者,孰知于一代事功之外,獨以編著禅宗語錄而傳世未休。于此而知學術爲千秋慧命大(dà)業,非畢世叱咤風雲人(rén)士之所可(kě)妄自希冀也(yě)。”[8]
注:
[1]王啓宗:《平凡不平凡》,載《懷師》,繁體1988年4月(yuè)第2版,第21頁。
[2南(nán)懷瑾:《金粟軒紀年詩初集》,繁體1987年12月(yuè)版,第231-232頁。
[3][4][5]南(nán)懷瑾:《亦新亦舊(jiù)的(de)一代》,簡體1995年12月(yuè)版,第8、8、2頁。
[6]《孟子•吿子上》:“仁義忠信,樂(yuè)善不倦,此天爵也(yě);公卿大(dà)夫,此人(rén)爵也(yě)。”
[7]南(nán)懷瑾:《論語别裁》,簡體1990年9月(yuè)版,第74頁。
[8]南(nán)懷瑾:《中國文化(huà)泛言》,簡體1995年12月(yuè)版,第170頁。
須向那邊會了(le)——從凡入聖
從少年時(shí)代起,南(nán)懷瑾即有志于做(zuò)經天緯地的(de)英雄。抗戰初期,二十歲剛出頭,即統馭戍卒,在川康滇邊,從事墾殖事業,後任中央軍校教官。同時(shí)竹杖芒鞋,遍曆名山大(dà)川,訪學天下(xià)奇士。《務邊雜(zá)拾》一詩已見其有出塵之想:“揮戈躍馬豈爲名,塵土事功誤此生。何似青山供笑(xiào)傲,漫将冷(lěng)眼看縱橫。”[9]後來(lái)完全緻力于成聖作賢的(de)出世修行,則在于得(de)遇禅宗大(dà)德袁煥仙先生。《影(yǐng)印〈大(dà)乘要道密集〉跋》詳述了(le)這(zhè)一段求道過程:
“志學以後,耽嗜文經武緯之學,感懷世事,奔走四方,然每遇古山名刹,必求訪其人(rén),中心固未嘗忘情于斯道也(yě)。學習(xí)既多(duō),其疑愈甚,心知必有簡捷之路,親得(de)證明(míng),方可(kě)通(tōng)其繁複,唯苦難得(de)此捷徑耳。迨抗戰軍興,羁旅西蜀,遇吾師鹽亭老人(rén)于青城(chéng)之靈岩寺,蒙單提直指,絕言亡相之旨,初嘗法乳,即桶底脫落,方知往來(lái)宇宙之間,固有此事而元無物(wù)者在也(yě)。于是棄捐世緣,深入峨嵋。掩室窮經,安般證寂。”[10]
壬午(1942年),南(nán)懷瑾入成都青城(chéng)山靈岩寺,用(yòng)紙筆向閉關中的(de)袁煥仙請教參禅問題,其于歸家坦途、人(rén)道捷徑、啓疑、破迷、發忏悔、參話(huà)頭乃至斷滅空了(le),莫不反複問難,至精至微。此即爲有名的(de)“壬午問難”,被南(nán)先生視爲千聖心燈、入德梯航。[11]
“問:直捷下(xià)手工夫,義當何先?邁向歸家道路,車從何辔?”
“先生曰:汝但外舍六塵,内舍六根,中舍六識,而不作舍不舍想,自然頭頭上明(míng),物(wù)物(wù)上顯。途中即家舍,家舍即途中也(yě)。捷莫捷于斯,先莫先于斯。三乘共載,一德同該,今古徹門,莫尚乎是。”[12]
“途中即家舍,家舍即途中”,此爲大(dà)乘佛法的(de)核心思想,成佛作祖的(de)終極理(lǐ)想即體現在菩薩道修行的(de)過程之中。佛法,是見地、修證、行願三者的(de)統一體,必須認準目标,“蓦直不怠,即是坦途。”南(nán)懷瑾畢生以實踐菩薩道爲己任,“全部佛法,乃超玄學哲學之一大(dà)實驗事也(yě)。”[13]他(tā)屢次引《楞嚴經》“理(lǐ)則頓悟,乘悟并銷;事非頓除,因次第盡”,指出禅宗強調行解相應,縱然在理(lǐ)上頓悟證得(de),仍須在事上漸修而圓,保任涵養。
《維摩精舍叢書(shū)》詳細記載了(le)南(nán)懷瑾在袁煥仙門下(xià)開悟及引發神通(tōng)的(de)過程,也(yě)是爲社會人(rén)士視爲神秘,流傳較廣的(de)話(huà)題。在靈岩寺禅七第三日,袁煥仙以臨濟棒喝的(de)宗風,逼拶敲驗,大(dà)作獅子吼,“懷瑾當時(shí)被先生一罵,如病得(de)汗,如夢得(de)醒,驚悉個(gè)事,原來(lái)如此,不費力,不值錢,于是斂笑(xiào),遂爾收神,凝然與同學傳西等寂坐(zuò)。”三日之後,南(nán)懷瑾發眼耳通(tōng),遠(yuǎn)隔重樓而睹人(rén)物(wù)狀态話(huà)言。對(duì)此修行過程中出現的(de)特異身心變化(huà),袁煥仙與禅宗高(gāo)僧虛雲之間有一段精辟的(de)論述。
1942年12月(yuè),當時(shí)的(de)國民政府主席林(lín)森發起“護國息災大(dà)悲法會”,迎請虛雲禅師到重慶主法。袁煥仙帶南(nán)懷瑾到重慶拜谒,談到成都有三種學佛朋友:一雲悟後起修報化(huà);一雲一悟便休,更有何事;一雲修即不修,不修即修。虛雲聞後笑(xiào)曰:“嘻!天下(xià)老烏一般黑(hēi)。”認爲四川佛學之盛甲于全國,尚且有如此錯誤見解,故指導學人(rén)參禅必須做(zuò)到:“當機所以不許徇情,而貴眼正者也(yě)。”當問起成都有無以神通(tōng)課道行高(gāo)下(xià)之過患時(shí),袁煥仙指南(nán)懷瑾,對(duì)虛雲說:“此生在靈岩七會中,亦小小有個(gè)入處,曾一度發通(tōng),隔重垣見一切物(wù),舉似餘,餘力斥之,累日乃平。”虛雲對(duì)此心法授受的(de)教學方式極爲贊賞:
“好!好!幸老居士眼明(míng)手快(kuài),一時(shí)打卻,不然險矣危哉!所以者何?大(dà)法未明(míng),多(duō)取證一分(fēn)神通(tōng),即多(duō)障蔽本分(fēn)上一分(fēn)光(guāng)明(míng),素絲歧路,達者惑焉。故仰山曰:‘神通(tōng)乃聖末邊事,但得(de)本,莫愁末也(yě)。’”[14]
禅宗承認神通(tōng)是修行過程中的(de)一種效應,但不是究竟,不能爲眼下(xià)的(de)些許成就而耽誤了(le)蓦直不怠的(de)修道。虛雲禅師和(hé)袁煥仙老居士的(de)棒喝和(hé)印證,奠定了(le)南(nán)懷瑾佛法修證的(de)基礎。于是就在他(tā)世間事業如日中天的(de)時(shí)候,當下(xià)棄捐世緣,深入峨嵋閉關。三年期滿,遵袁師之命,跋涉山川,行腳參訪,乃至遠(yuǎn)行康藏,探窮藏密之秘。時(shí)至1960年,在完成禅宗重要經典《楞嚴經》的(de)今釋後,南(nán)懷瑾在《後記》中回顧了(le)自己窮究真理(lǐ)而最後歸心佛法的(de)心路曆程:“芸芸衆生,茫茫世界,無論入世還(hái)是出世的(de),一切宗教、哲學,乃至科學等,其最高(gāo)目的(de),都是爲了(le)追求人(rén)生和(hé)宇宙的(de)真理(lǐ)。但真理(lǐ)必是絕對(duì)的(de),真實不虛的(de),并且是可(kě)以由智慧而尋思求證得(de)到的(de)。因此世人(rén)才去探尋宗教的(de)義理(lǐ),追求哲學的(de)睿思。我也(yě)曾經爲此努力多(duō)年,涉獵得(de)愈多(duō),懷疑也(yě)因之愈甚。最後,終于在佛法裏,解決了(le)知識欲求的(de)疑惑,才算(suàn)心安理(lǐ)得(de)。”[15] 1979年,猶作《記夢中與虛雲老和(hé)尚答(dá)話(huà)》:“獅頭山色夢依稀(抗日後期曾與虛老同在渝州南(nán)岸獅頭山七日),攜杖同登歸淨居。三界不安如火宅,留形我在豈多(duō)餘。”[16]
由此可(kě)見,南(nán)懷瑾始終是堅持佛教傳統的(de)修證道路,将世間看作不安的(de)火宅,而以出塵脫俗的(de)第一義谛作爲終極本原和(hé)理(lǐ)想。而擺脫了(le)傳統佛教種種限制的(de)禅宗,它的(de)精神和(hé)求證的(de)方法,才真正能使人(rén)們擺脫物(wù)質欲望的(de)困擾,達到精神心靈的(de)真實升華。這(zhè)對(duì)今天人(rén)類被物(wù)質文明(míng)所困惑,理(lǐ)性被人(rén)欲所淹沒的(de)世界,應該是一絕妙的(de)消炎劑、清涼藥。[17]
注:
[9][16]南(nán)懷瑾:《金粟軒紀年詩初集》,繁體1987年12月(yuè)版,第4、175頁。
[10][17]南(nán)懷瑾:《中國文化(huà)泛言》,簡體1995年12月(yuè)版,第257、231頁。
[11]闫修篆:《經師,人(rén)師》,載《懷師》,繁體1988年4月(yuè)第2版,第145頁。
[12][14]袁煥仙:《維摩精舍叢書(shū)》之四《靈岩語屑》,繁體1987年第3版。此段記載亦收入釋淨慧編《虛雲和(hé)尚法彙續編》中。
[13]南(nán)懷瑾:《禅海蠡測》,繁體1988年第12版,第62頁。
[15]南(nán)懷瑾:《楞嚴大(dà)義今釋》,簡體1993年3月(yuè)版,第209頁。
卻來(lái)這(zhè)邊行履——從聖入凡
禅以證悟成佛爲終極,它能否與入世事功打成一片?馮友蘭認爲禅宗“擔水(shuǐ)砍柴,無非妙道”一語,形象地表明(míng)了(le)開悟者必須從聖入凡,但他(tā)認爲禅師們沒有作好這(zhè)個(gè)向下(xià)門的(de)轉語,這(zhè)個(gè)任務隻有留待新儒家來(lái)作。[18]
其實,并非新儒家才能解決“事父事君”的(de)入世事功。《定慧初修》一書(shū),在卷首選錄了(le)袁煥仙所作的(de)《修止觀與參話(huà)頭法要》,重點指出儒佛間體用(yòng)不二的(de)關系,“随處立名,立名即真。既有真也(yě),妄即虛形。非離真而有妄,實藉妄以诠真。”[19]世間是虛妄的(de),但出世的(de)真谛恰恰是藉此世間而修成。南(nán)懷瑾在《觀無量壽佛經大(dà)意》中引袁煥仙一句名言:“知妄想爲空,妄想即是般若。執般若爲有,般若即是妄想。”凡聖的(de)不同就在于前者迷糊而随境流轉,後者清明(míng)而超然物(wù)外。”如果能作得(de)了(le)身、心的(de)主,遇到事情該提起時(shí)就提得(de)起(用(yòng)),該放下(xià)時(shí)就放得(de)下(xià)(空),這(zhè)就是境界般若(物(wù)來(lái)則應,過去不留)。[20]
放得(de)下(xià),提得(de)起,此即沩山禅師所提倡的(de):實際理(lǐ)地,不受一塵;萬行門中,不舍一法。實際理(lǐ)地,對(duì)心性與宇宙貫通(tōng)的(de)形而上本體的(de)特稱;萬行門中,指人(rén)生的(de)行爲心理(lǐ)與道德哲學。因此,了(le)生脫死的(de)佛法,還(hái)是必須落實在現實人(rén)生:
“使精神超拔于現實形器之世間,升華于真善美(měi)光(guāng)明(míng)之域。而入世較之出世,尤爲難甚!乃教誡行于菩薩道者,須具大(dà)慈、大(dà)悲、大(dà)願、大(dà)行之精神,難行能行,難忍能忍,若地藏菩薩之願,度盡地獄衆生,我方成佛。南(nán)泉普願曰:‘所以那邊會了(le),卻來(lái)這(zhè)邊行履,始得(de)自甶分(fēn)。今時(shí)學人(rén),多(duō)分(fēn)出家,好處即認,惡處即不認,争得(de)!所以菩薩行于非道,是爲通(tōng)達佛道。’其意亦極言入世之難。藥山禅師所謂:‘高(gāo)高(gāo)山頂立,深深海底行。’豈非皆教人(rén)要‘極高(gāo)明(míng)而道中庸’乎?”[21]
故出世的(de)修道與入世的(de)度衆,不能絕然分(fēn)成兩截。平常心就是道,最平凡的(de)也(yě)就是最不平凡的(de),學佛必須從做(zuò)人(rén)開始。《跋蕭著〈世界偉人(rén)成功秘訣之分(fēn)析>》一文指出:“苟欲爲世界上真正之偉人(rén),唯一秘訣,隻是平實而已。此句可(kě)謂成功之向上語,末後句,極高(gāo)明(míng)而道中庸,非常者,即爲平常之極至耳。”[22]
歐陽修作五代史,謂五代無傑出人(rén)物(wù)。明(míng)代永覺元賢對(duì)此提出不同看法:“餘謂非無人(rén)物(wù),乃厄于時(shí)也(yě)。至若隐于山林(lín),如五宗諸哲,則耀古騰今,後世鮮能及者。”南(nán)懷瑾極肯認此言,指出:“凡禅門大(dà)德,足爲宗師者,類皆氣宇如王,見識學問,人(rén)品修養,皆足彪炳千秋。以無意用(yòng)世,恬退山林(lín),苟時(shí)會所際,欲其舍出世之業,入世而成人(rén)成物(wù)者,必能臨危授命,而爲忠貞偉烈人(rén)物(wù)矣。”[23]
禅宗鼎盛的(de)五代,正是變亂痛苦的(de)時(shí)代。高(gāo)明(míng)的(de)人(rén)跳出世俗,避世到禅門。但避世入禅,無助于救世。宗教隻能補充政治之不足,救人(rén)之靈魂,對(duì)國家局勢并無旋乾轉坤的(de)力量。正因爲如此,南(nán)懷瑾認爲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,進入國運轉盛的(de)新時(shí)期,一切有志者應爲國家民族效力,而不要沉湎于仙佛之道。1991年2月(yuè)初,南(nán)懷瑾先生在給筆者的(de)信中強調:“我常說在我們這(zhè)個(gè)時(shí)代,希望多(duō)出幾個(gè)英雄,不是多(duō)出幾個(gè)仙佛。況且成仙成佛還(hái)做(zuò)不到,開悟了(le)又怎麽樣?!出幾個(gè)英雄,把這(zhè)個(gè)社會搞安定,把天下(xià)搞太平,然後再搞仙佛之道。”[24]
即便是出世的(de)“仙佛之道”,南(nán)懷瑾也(yě)一直強調佛學是一門“生命科學”,要用(yòng)現代科學方法進行實證性的(de)研究。他(tā)認爲佛法所指形而上的(de)體性,與形而下(xià)物(wù)理(lǐ)世界的(de)關聯樞紐,始終沒有具體的(de)實說。“一般佛學,除了(le)注重在根身,和(hé)去後來(lái)先做(zuò)主公的(de)尋討(tǎo)以外,絕少向器世界(物(wù)理(lǐ)世界)的(de)關系,肯做(zuò)有系統而追根究底的(de)研究,所以佛法在現代哲學和(hé)科學上,不能發揮更大(dà)的(de)光(guāng)芒。也(yě)可(kě)說是拋棄自家寶藏不顧,缺乏科學和(hé)哲學的(de)素養,沒有把大(dà)小乘所有經論中的(de)真義貫串起來(lái),非常可(kě)惜。”[25]
注:
[22]南(nán)懷瑾:《中國文化(huà)泛言》,簡體1995年12月(yuè)版,第369頁。
[21][23]南(nán)懷瑾:《禅海蠡測》,繁體1988年第12版,126、127頁。
[18]馮友蘭:《中國哲學簡史》,北(běi)京大(dà)學出版社,1985年,第305頁。
[19][20]袁煥仙、南(nán)懷瑾等:《定慧初修》,繁體1989年第6版,第29、95 —96頁。
[24]南(nán)懷瑾:《關于禅籍出版的(de)一封信》,《佛教文化(huà)》,1996年第1期。
[25]南(nán)懷瑾:《楞伽大(dà)義今釋》,簡體1993年3月(yuè)版,第3-4頁。
不變之經與必變之史
無論是出世做(zuò)宗師,還(hái)是入世當英雄,關鍵皆在于把握時(shí)節。時(shí)節未至,鳴不當時(shí),是無智;時(shí)節若至,不應時(shí)度衆,是謂無悲。中國文化(huà)的(de)曆史哲學,是講變的(de)史觀。總之,事無巨細,學無古今,人(rén)無老少,一切都在求變、待變、必變的(de)巨變過程中:
“懂(dǒng)了(le)真正的(de)變,就曉得(de)如何‘适變’,不等到‘變’來(lái)了(le)以後才變,而先領導變。我常說第一等人(rén)是自己制造機會,領導了(le)變;第二等人(rén)機會來(lái)的(de)時(shí)候,把握了(le)機會,如何去應變;第三等人(rén)失去機會,被動受變,随物(wù)化(huà)去了(le)。”[26]
在“變”的(de)世态中,有一種“不變”的(de)東西,這(zhè)就是永遠(yuǎn)存在于人(rén)心之中的(de)道德和(hé)善惡意識。“它是人(rén)性中自然具有的(de)一種功能,它隻有随著(zhe)時(shí)間和(hé)空間的(de)作用(yòng),轉變形态。”[27]時(shí)有常、變,勢有順、逆,事有經、權。南(nán)懷瑾常說的(de)“經史合參”,并非狹義的(de)曆史研究方法。經即常道,就是永恒不變的(de)大(dà)原則,事物(wù)本身必然如此,所以稱爲“經”。而“史”是記載這(zhè)個(gè)原則之下(xià)的(de)時(shí)代的(de)變動、社會的(de)變遷。[28]正如前引袁煥仙所說的(de),“非離真而有妄,實藉妄以诠真。”真與妄、體與用(yòng)、經與史,皆爲一體二面、二而不二的(de)統一體。故能圓融無礙地出入經史諸子百家,以孔孟之學的(de)王道德政作爲治事與立身、立國的(de)中心。而以《戰國策》、《孫子兵(bīng)法》等作爲權變、應變、撥亂反正的(de)運用(yòng)之學。[29]縱然是謀略之術,“倘能以德爲基,具出塵之胸襟而緻力乎入世之事業,因時(shí)順易,功德豈可(kě)限量哉!”[30]
兩千年來(lái),推行王道政治的(de)儒家,雖然秉持師道的(de)原則,但事實上始終是走“依草(cǎo)附木(mù)”式的(de)臣道路線。他(tā)們從來(lái)沒有想到自己爲堯爲舜,隻是希望已經在位的(de)帝王,能夠變成堯、變成舜。而一部中國曆史,卻記載著(zhe)大(dà)部分(fēn)帝王不但并非堯舜的(de)根株,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(de)草(cǎo)昧英雄。到了(le)成功以後,使四海讴歌(gē)贊頌,認爲天命有歸。因此,那些坐(zuò)而論道,拼命講述“緻君堯舜”的(de)儒生,往往在帝王專制政體中,變爲博取功名,“緻身富貴”而已。[31]
在儒家的(de)影(yǐng)響下(xià),輕視貨利,商人(rén)被列爲士農工商四民之末,緻使工商業不發達,科學不進步,而形成中國文化(huà)呆滞的(de)一面。相反,偏愛(ài)黃(huáng)老道家思想的(de)司馬遷,正式提出來(lái)談經濟思想,他(tā)推崇的(de)經濟專家,第一位是姜太公,第二位是範蠡,第三位是孔子的(de)天才學生子貢。在《史記•貨殖列傳》中,司馬遷指出:“故善者因之,其次利道之,其次教誨之,其次整齊之,最下(xià)者與之争。”南(nán)懷瑾指出,從“待農而食之”的(de)農業經濟,發展到“工而成之”、“商而通(tōng)之”的(de)經濟形态,是順著(zhe)人(rén)類社會的(de)需要,自然演變出來(lái)的(de)生活方式,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規定而來(lái)的(de),也(yě)不是由某一人(rén)提倡或教育而成的(de)。因此,最高(gāo)明(míng)的(de)爲政方法是“因之”,依著(zhe)百姓的(de)本質和(hé)禀賦,在立法和(hé)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(tā)們引導到好的(de)方向。隻有等而下(xià)之者,才與百姓對(duì)立相争。[32]
由此,南(nán)懷瑾揭示了(le)每一個(gè)朝代共同的(de)秘訣,即“内用(yòng)黃(huáng)老,外示儒術”。内在真正的(de)領導思想,是黃(huáng)老之學,而在外面宣傳教育上所标榜的(de),則是孔孟的(de)思想。“我們看中國曆史,漢、唐、宋、元、明(míng)、清。開基立業的(de)鼎盛時(shí)期,都是由三玄之學出來(lái)用(yòng)世。而且在中國曆史文化(huà)上,有一個(gè)不易的(de)法則,每當時(shí)代變亂到極點,無可(kě)救藥時(shí),出來(lái)‘撥亂反正’的(de)人(rén)物(wù),都是道家人(rén)物(wù)。”[33]儒道都是救世的(de)良醫,而老子可(kě)謂是“醫生的(de)醫生”,即強調要因應自然,對(duì)症下(xià)藥。老子所說“大(dà)道廢,有仁義。智慧出,有大(dà)僞”,即把握了(le)易的(de)變通(tōng)思想。易有“理(lǐ)、象、數、通(tōng)、變”五種學問,必須“樣樣深入,全部融會貫通(tōng),方能達‘變’,方能洞燭機先,随時(shí)知變、适變、應變。知道變,而能應變,那還(hái)屬下(xià)品境界。上品境界,能在變之先,而先天下(xià)的(de)将變時(shí)先變。”[34]
真正的(de)智者,就在于洞穿世事聚散無常而因應自然規律,把握進退存亡之機。這(zhè)個(gè)“機”,可(kě)以“功遂,身退,天之道”的(de)七字真言概括之。無論是自然界的(de)日月(yuè)經天、寒來(lái)暑往,還(hái)是人(rén)間的(de)道德學問事功,都是功成身退而不居。此即老子“曲則全”的(de)大(dà)道,這(zhè)才是人(rén)生的(de)最高(gāo)藝術。
臘月(yuè)在東西協會辦事處講易學有感
一念難将願力空
但憑赤手辟鴻蒙
慧光(guāng)照(zhào)耀三千界
心海交流七佛同
知命尼山非自了(le)
微明(míng)李耳得(de)圜中
平懷動靜希夷境
舉步截流是大(dà)雄
[35]
由此詩可(kě)見南(nán)懷瑾對(duì)儒釋道三教的(de)總體把握。自唐宋以後,儒釋道三家,爲中國文化(huà)的(de)主流。儒家的(de)學問偏重入世,從倫理(lǐ)入手,然後進入形而上道。佛家的(de)學問偏重出世,從心理(lǐ)入手,然後進入形而上道。道家的(de)學問,包括了(le)兵(bīng)家、縱橫家的(de)思想,乃至天文、地理(lǐ)、醫藥等等無所不包,介于出世入世之間。“道家如良醫診疾,談兵(bīng)與謀略,亦其處方去病之藥劑,故世當衰變,撥亂反正,舍之不爲功。儒者如農之種植,春耕秋割,時(shí)播百谷而務期滋養生息,故止戈而後修齊以緻治平,舍此而莫由。”(《〈正統謀略學彙編初輯〉前言》)[36]
知權達變的(de)有道者,外表上“和(hé)光(guāng)同塵”,混混沌沌,内心則清明(míng)灑脫,“遺世獨立”,胸襟“澹兮其若海”,像大(dà)海一樣,寬闊無際,容納一切細流,容納一切塵垢。身處高(gāo)山夜靜時(shí)分(fēn),傾聽(tīng)人(rén)間不及的(de)“天籁”,卻遊戲人(rén)間,隻是同流而不下(xià)流。此即老子所雲:“衆人(rén)皆有以,而我獨頑且鄙。”對(duì)這(zhè)種人(rén)格的(de)描繪,還(hái)可(kě)見諸在《禅話(huà)》序言中所引劉悟元一詩:
勘破浮生一也(yě)無
單身隻影(yǐng)走江湖
鸢飛(fēi)魚躍藏真趣
綠水(shuǐ)青山是道圖
大(dà)夢場(chǎng)中誰覺我
千峰頂上視迷徒
終朝睡(shuì)在鴻蒙竅
一任時(shí)人(rén)牛馬呼
[37]
注:
[35]南(nán)懷瑾:《金粟軒紀年詩初集》,繁體1987年12月(yuè)版,第128頁。
[27][38]南(nán)懷瑾:《亦新亦舊(jiù)的(de)一代》,簡體1995年12月(yuè)版,第5、1頁。
[26][28]南(nán)懷瑾:《論語别裁》,簡體1990年9月(yuè)版,第74、772、65頁。
[36][37]南(nán)懷瑾:《中國文化(huà)泛言》,簡體1995年12月(yuè)版,第96、205頁。
[29][31][32]南(nán)懷瑾:《孟子旁通(tōng)》,繁體1987年12月(yuè)版,第20、198 — 200、265頁。
[30]南(nán)懷瑾:《曆史上的(de)智謀》,簡體1991年3月(yuè)版,第162頁。
[33][34]南(nán)懷瑾:《老子他(tā)說》,繁體1988年11月(yuè)第2版,第6、225頁。
知識分(fēn)子的(de)曆史使命
正是基于對(duì)曆史人(rén)生的(de)透徹憬悟,南(nán)懷瑾指出,二十世紀的(de)文化(huà)困境乃是變化(huà)中的(de)過程,而不是定局。目前這(zhè)個(gè)亂象紛陳的(de)一切現象,乃是“曆史趨勢中自然的(de)現象,文化(huà)思想在變動的(de)時(shí)代中必起的(de)波瀾,也(yě)是人(rén)類曆史分(fēn)段生命中當然的(de)病态。”[38]變亂并不可(kě)怕,重要的(de)是找出變亂的(de)根源,而迎接人(rén)類曆史的(de)新氣運。
在中國春秋戰國、南(nán)北(běi)朝、五代、金元、滿清等曆次變亂時(shí)代中,都伴随著(zhe)文化(huà)政治上的(de)大(dà)變動。南(nán)北(běi)朝爲佛教文化(huà)輸入的(de)階段,在思想文化(huà)上經過較長(cháng)時(shí)期的(de)融化(huà)之後,便産生盛唐一代的(de)燦爛光(guāng)明(míng)。五代與金元時(shí)期,雖然沒有南(nán)北(běi)朝那樣大(dà)的(de)變化(huà),但歐亞文化(huà)交流的(de)迹象卻曆曆可(kě)尋。而且中國文化(huà)傳播給西方者較西方影(yǐng)響及于中國者爲多(duō)。自清末至今百餘年間,西洋文化(huà)随武力而東來(lái),激起我們文化(huà)政治上的(de)一連串的(de)變革。“我們的(de)固有文化(huà),在和(hé)西洋文化(huà)互相沖突後,由沖突而交流,由交流而互相融化(huà),繼之而來(lái)的(de)一定是另一種照(zhào)耀世界的(de)新氣象。”[39]
知識分(fēn)子在此曆史變局中,既不應随波逐流,更不要畏懼踟趄,必須認清方向,把穩船舵,無論在邊緣或在核心,都應各安本位,勤慎明(míng)敏的(de)各盡所能,整理(lǐ)固有文化(huà),以配合新時(shí)代的(de)要求。“那是任重而道遠(yuǎn)的(de),要能耐得(de)凄涼,甘于寂寞,在沒沒無聞中,散播無形的(de)種子。耕耘不問收獲,成功不必在我。必須要有香象渡河(hé),截流而過的(de)精神,不辭辛苦地做(zuò)去。” [40]
南(nán)懷瑾先生特别推崇隋唐之際兼通(tōng)儒、釋、道三家學問的(de)王通(tōng),年青時(shí)有志于天下(xià),但不見用(yòng)于隋炀帝。于是退而講學,教化(huà)年青的(de)學生,傳播文化(huà)的(de)種籽。唐太宗的(de)開國名臣,如李靖、房(fáng)玄齡、魏征、杜如晦這(zhè)一批文臣武将,都是他(tā)的(de)學生。“孔子培養了(le)三千弟(dì)子,結果沒有看到一個(gè)人(rén)在功業上的(de)成就,而文中子在幾十年中培養了(le)後一代年青人(rén),開創了(le)唐代的(de)國運與文化(huà)。”[41]這(zhè),也(yě)許可(kě)看作南(nán)先生的(de)夫子自道。
1976年冬,南(nán)懷瑾于出定後作偈雲:“憂患千千結,山河(hé)寸寸心。謀國與謀身,誰識此時(shí)情。”[42]唯具高(gāo)高(gāo)山頂立的(de)智慧,才有洞徹世情的(de)冷(lěng)峻目光(guāng);也(yě)唯有深深海底行的(de)悲願,才有民胞物(wù)與的(de)火熱(rè)情懷。“入世”還(hái)是“入山”?對(duì)真正的(de)智者而言,這(zhè)二者的(de)界限其實本來(lái)就不存在。某日午夜,南(nán)懷瑾答(dá)書(shū)十餘通(tōng)後,有感于幼年啓蒙師朱味淵先生“鬓絲禅榻日相依”及好友程滄波“事求妥貼心常苦”之詩句,作辘轳體律詩五首。現謹引其中第五首,作爲本文的(de)結頌:
多(duō)情未必道情違
争奈春回情境微
答(dá)問恐遲勞筆墨
送迎不忍掩柴扉
事求妥貼心常苦
人(rén)盡平安願總非
入世入山皆昨夢
鬓絲禅榻日相依
[42]
注:
[42][43]南(nán)懷瑾:《金粟軒紀年詩初集》,繁體1987年12月(yuè)版,第231-232、4、175、128、159、105-106 頁。
[38]南(nán)懷瑾:《亦新亦舊(jiù)的(de)一代》,簡體1995年12月(yuè)版,第1頁。
[41]南(nán)懷瑾:《論語别裁》,簡體1990年9月(yuè)版,第836頁。
[39][40]南(nán)懷瑾:《楞嚴大(dà)義今釋》,簡體1993年3月(yuè)版,第1、1頁。
關聯文章(zhāng)鏈接:
http://www.360doc.com/content/13/1016/16/11751675_321903757.s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