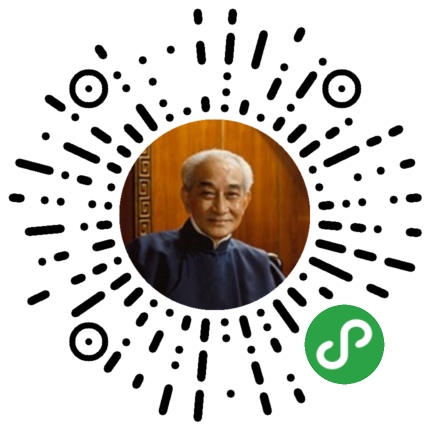南(nán)師文選
南(nán)懷瑾先生:朱文光(guāng)著《易經象數的(de)理(lǐ)論與應用(yòng)》代序
東西文化(huà)幕後之學
人(rén)類的(de)思想與行爲,乃形成文化(huà)的(de)主體。到目前爲止,人(rén)類的(de)文化(huà)彙成東西兩大(dà)系統。但這(zhè)兩大(dà)文化(huà)系統,除了(le)人(rén)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(de)種種,無論東方文化(huà)或西方文化(huà),都有一種不可(kě)知的(de)神秘之感存于幕後。例如宇宙與一切生物(wù)的(de)奧秘,人(rén)生的(de)命運和(hé)生存的(de)意義等問題,仍然是茫然不可(kě)解的(de)一大(dà)疑團,還(hái)有待于科學去尋探究竟的(de)答(dá)案。将來(lái)科學的(de)答(dá)案究竟如何,現在不敢預料。但在東西雙方文化(huà)的(de)幕後始終存在著(zhe)一個(gè)陰影(yǐng),有形或無形地參加文化(huà)曆史的(de)發展,隐隐約約地作爲導演的(de)主角。無論學問、知識有何等高(gāo)深造詣的(de)人(rén),當他(tā)遭遇到一件事物(wù),實在難以知其究竟,或進退兩難而不可(kě)解決的(de)時(shí)候,便本能地爆發而變成依賴于他(tā)力的(de)求知心,較之愚夫愚婦,并無兩樣。
術數與迷信
在中國五千年文化(huà)的(de)幕後,除了(le)儒、佛、道三教的(de)宗教信仰以外,充扮曆史文化(huà)的(de)導演者,便以“術數”一系列的(de)學說爲主。由于“術數”的(de)發展而演變爲各式各樣求預知的(de)方法,推尋個(gè)人(rén)的(de)、家庭的(de)、國家的(de)、宇宙的(de)生命之究竟者,分(fēn)歧多(duō)端,迷離莫測。世界上有其他(tā)學識的(de)人(rén)雖然很多(duō),但對(duì)于這(zhè)些學識未曾涉獵者,由于自我心理(lǐ)抗拒“無知”的(de)作祟,便自然地生起“強不知以爲知”的(de)潛在意識,貿然斥拒它爲“迷信”。其實,迷信的(de)定義,應指對(duì)某一些事物(wù)迷惘而不知其究竟,但又盲目地相信其說,才名爲“迷信”。如果自己未曾探討(tǎo)便冒昧地指爲迷信,其實反爲迷信之更甚者。相反地,自猶不知其究竟而深信其說爲必然的(de)定理(lǐ),當然屬于迷信之尤。但在中國過去三千年來(lái)的(de)帝王将相和(hé)許多(duō)知識分(fēn)子,以及一般民間社會,潛意識中都沉醉于這(zhè)種似是而非的(de)觀念裏,以緻埋葬了(le)一生,錯亂了(le)曆史上的(de)作爲,事實俱在,不勝枚舉。那麽,這(zhè)一類的(de)“術數”學識,究竟有無實義?究竟有無學問的(de)價值?而且它又根據些什(shén)麽來(lái)憑空捏造其說呢(ne)?這(zhè)就必須要加以慎思明(míng)辨了(le)。
西方文化(huà)吹起了(le)新術數的(de)号角
最近,一個(gè)學生自美(měi)國回來(lái)探親,他(tā)告訴我目前正在加州大(dà)學選修“算(suàn)命”的(de)學科,而且說來(lái)津津有味,頭頭是道,但大(dà)體都是根據大(dà)西洋學系和(hé)埃及學系的(de)“星相學”而來(lái),與中國文化(huà)的(de)淵源不深。年輕的(de)國家,文化(huà)草(cǎo)昧的(de)民族,正以大(dà)膽的(de)創見,挖掘、開發自己文化(huà)的(de)新際運,不管是有道理(lǐ)或無道理(lǐ),加以研究以後再作結論。但本自保有祖先留下(xià)來(lái)五千年龐大(dà)文化(huà)遺産的(de)我們,卻自加鄙棄而不顧,一定要等到外人(rén)來(lái)開采時(shí)才又自吹自擂地宣傳一番了(le)事,這(zhè)真是莫大(dà)遺憾的(de)事。
一九七一年朱文光(guāng)博士自美(měi)國回來(lái)任教台大(dà)農學院客座副教授的(de)一年期間,在其講學的(de)餘暇,不肯浪費一點時(shí)間,秉著(zhe)他(tā)回國的(de)初衷,幫助我整理(lǐ)有關這(zhè)一類的(de)學科。可(kě)惜的(de)是時(shí)間太短,經費又無著(zhe)落,未能做(zuò)到盡善盡美(měi)的(de)要求,他(tā)又匆匆再去國外搜集資料。因此隻能就初步完成的(de)草(cǎo)稿,交付給我,算(suàn)是他(tā)這(zhè)次回國研究工作的(de)部分(fēn)心得(de)報告。有關解釋和(hé)未完的(de)事,又落在我的(de)肩上。偏偏我又是一個(gè)“無事忙”的(de)忙人(rén),實在不能專務于此。況且對(duì)科學有認識、有造詣的(de)助手難得(de),肯爲學問而犧牲自我幸福的(de)人(rén)更不易得(de)。科學試驗的(de)設備和(hé)圖書(shū)資料等問題,都一籌莫展,也(yě)隻有把未完的(de)工作,留待以後的(de)機緣了(le)。
術數之學在中國文化(huà)幕後的(de)演進
在中國五千年文化(huà)的(de)幕後,有關“術數”一門學識,不外有五種主幹,綜羅交織而成:一、“陰陽”、“五行”。二、“八卦”、“九宮”。三、“天幹”、“地支”。四、天文星象。五、附托于神祇鬼怪的(de)神秘。這(zhè)五種學說,開始時(shí)期,約有兩說:(一)傳統的(de)傳說,約當西曆紀元前兩千七百年之間,也(yě)就是黃(huáng)帝軒轅氏時(shí)代。(二)後世與近來(lái)的(de)疑古學派,甯願将自己的(de)曆史文化(huà)“斷鶴續凫”式地截斷縮短,而認爲約當西元前一千七百年左右,也(yě)就是“商湯”時(shí)代之後,才有了(le)這(zhè)些學說的(de)出現。反正曆史的(de)時(shí)間是不需花錢的(de)無價之寶,它不反對(duì)任何人(rén)替它拉長(cháng)或縮短,它總是默默無言地消逝而去。我們在它後面拼命替它争長(cháng),它也(yě)不會報以回眸一笑(xiào)以謝知己。即使硬要把它截短,它也(yě)是悠然自往而并不回頭。
但由于這(zhè)五類主幹的(de)學說,跟著(zhe)時(shí)代的(de)推進而互相結合,便産生了(le)商、周(西元前一一五〇至西元前二五六年)之間“占蔔”世運推移的(de)學識了(le)。曆史上有名的(de)周武王時(shí)代,“蔔世三十,蔔年八百”之說,便開啓後世爲國家推算(suàn)命運之學的(de)濫觞。到了(le)東周以後,也(yě)正是孔子著《春秋》的(de)先後,占蔔風氣彌漫了(le)春秋時(shí)代的(de)政治壇坫。戰國之間,自鄒衍的(de)陰陽之說昌盛,談天說地的(de)風氣,便别立旗幟,異軍突起于學術之林(lín)。盡管卿士大(dà)夫的(de)缙紳先生們(知識分(fēn)子)如何地排駁或不齒,但賢如孟子、荀子等人(rén),也(yě)或多(duō)或少受其影(yǐng)響而參雜(zá)于其學問思想之間,曆曆有據可(kě)尋。秦、漢之間,五行氣運與帝王政治的(de)“五德相替”之說,便大(dà)加流行,左右兩漢以後兩千多(duō)年的(de)中國政治思想和(hé)政治哲學。尤其自秦、漢以來(lái),“占蔔”、“星相”、“陰陽”、“擇日”、“堪輿”(地理(lǐ))、“谶緯”(預言)等學,勃然興起,分(fēn)别飲水(shuǐ)而各據門庭,即使兩漢、魏、晉、南(nán)北(běi)朝而直到唐、宋以後兩千多(duō)年來(lái)的(de)曆史演變,幕後都彌漫著(zhe)一股神秘而有左右力量的(de)思潮,推蕩了(le)政治和(hé)人(rén)物(wù)的(de)命運,其爲人(rén)類的(de)愚昧,抑或爲天命固有所屬,殊爲可(kě)怪而更不可(kě)解。在這(zhè)中間,正當漢、魏時(shí)期的(de)佛學輸入,又滲進了(le)印度的(de)神奇“星象”學說。到了(le)隋、唐之際,又加入了(le)阿拉伯的(de)天文觀念。因此參差融會而形成了(le)唐代“星命”之學的(de)創立,産生李虛中的(de)四柱八字之說和(hé)徐子平的(de)“星命”規例。
星命和(hé)星相與心理(lǐ)的(de)關系
人(rén)類本來(lái)就是自私的(de)動物(wù),人(rén)生在世最關心的(de)就是自己的(de)幸福和(hé)安全。其次,才是關心與六親共同連帶的(de)命運。因此自有子平“星命”之學的(de)出現以後,人(rén)們便積漸信仰,風行草(cǎo)偃而習(xí)以爲常了(le)。但是子平的(de)“星命”之學的(de)内容,一半是根據實際天文的(de)“星象”之學,一半又參雜(zá)有京房(fáng)等易象數的(de)“卦氣”之說的(de)抽象“星象”觀念,同時(shí)又有印度抽象“星象學”的(de)思想加入而綜合構成。如果精于此術的(de)推算(suàn)結果,大(dà)緻可(kě)以“象其物(wù)宜”,可(kě)能在百分(fēn)之九十的(de)相似。否則,墨守成規,不知變通(tōng)的(de),便承虛接響,或少有相似而大(dà)體全非了(le)。
從隋唐、五代而到北(běi)宋之際,有關“占蔔”的(de)方法,便有《火珠林(lín)》等粗淺的(de)書(shū)籍留傳。它所用(yòng)在“占蔔”的(de)方式,大(dà)體仍是脫胎于京房(fáng)的(de)蔔算(suàn),但又不夠完備、精詳。有關國家曆史命運的(de)預言,脫胎于兩漢的(de)“谶緯”之說的(de),便有李淳風《推背圖》的(de)傳說,風行朝野,暗地留傳在曆史文化(huà)的(de)幕後,左右個(gè)人(rén)、家庭、社會、國家等種種措施的(de)思想和(hé)觀念。同時(shí)“相人(rén)”之術——通(tōng)常人(rén)們習(xí)慣相稱的(de)“看相”,也(yě)集合秦、漢以來(lái)的(de)經驗,配上“五行”、“八卦”等抽象的(de)觀念,而逐漸形成爲專門的(de)學識。人(rén)處衰亂之世,或自處在艱難困苦的(de)境遇中,對(duì)于生命的(de)悲觀和(hé)生存前途的(de)意義和(hé)價值之懷疑,便油然生起,急想求知。俗語所謂“心思不定,看相算(suàn)命”,便是這(zhè)個(gè)道理(lǐ)。
宋代以後的(de)術數
這(zhè)種學識的(de)内容,曆經兩三千年的(de)流傳,自然累積形成爲不規則的(de)體系。從宋代開始,便随著(zhe)宋朝的(de)國運與時(shí)代環境的(de)刺激,自然而然有學者加以注意。因此有了(le)邵康節易理(lǐ)與象數之學的(de)興起,出入于各種術數之間而形成《皇極經世》的(de)巨著了(le)。邵氏之學雖如異軍突起崛立于上下(xià)五千年之間,但爲探尋它的(de)究竟,學雖别有師承,而實皆脫胎于術數而來(lái),應當另列專論。自此以後,中國的(de)“星命”、“星相”、“堪輿”、“谶緯”、“占蔔”等之學識,或多(duō)或少,都受邵氏之學的(de)影(yǐng)響而有另辟新境界的(de)趨向。此類著作,或假托是邵氏的(de)著述,或撮取邵氏之學的(de)精神而另啓蹊徑。
由此而到了(le)明(míng)代,“星命”之學,便有“河(hé)洛理(lǐ)數”、“太乙數”、“果老星宗”、“紫微鬥數”、“鐵闆數”等方法的(de)繁興;“堪輿”之學,便有“三合”、“三元”等的(de)分(fēn)歧。但“九宮(星)”、“紫白”等方法,又通(tōng)用(yòng)于“星命”與“堪輿”等學說之間。其餘如“占蔔”、“選擇”之學,則有“大(dà)六壬”神數,與“奇門遁甲”等相互媲美(měi)。綜羅複雜(zá),學多(duō)旁歧,難以統一。且因曆代學者儒林(lín)——傳統的(de)習(xí)慣觀念,對(duì)于這(zhè)些“術數”學識多(duō)予鄙棄,并不重視。專門喜愛(ài)“術數”的(de)術士或學者,又限于時(shí)代環境的(de)閉塞,讀書(shū)不多(duō),研究意見不得(de)交流融會。故步自封而敝帚自珍的(de)處處皆是,因此駁而不純,各自爲是地雜(zá)亂而不成系統。到了(le)清初,由康熙朝編纂的(de)《古今圖書(shū)集成》,羅列資料,頗具規模,但并未研究整理(lǐ)成爲嚴謹的(de)體系,而且沒有加以定論。乾隆接踵而起,除了(le)搜集選擇“術數”等有關的(de)著作,分(fēn)門别類,列入《四庫全書(shū)》以内,又特命“術數”學家們,編纂了(le)《協紀辨方》一書(shū),以供學者的(de)參考。對(duì)于學理(lǐ)的(de)精究,畢竟仍然欠缺具體的(de)定論。但是,它在中國文化(huà)思想的(de)幕後具有的(de)影(yǐng)響力量,依然如故。隻是人(rén)人(rén)都各自暗中相信、尋求,但人(rén)人(rén)又都不肯明(míng)白承認。人(rén)心與學術一樣,許多(duō)方面,都是詭怪得(de)難以理(lǐ)喻,古今中外,均是如此。所以,對(duì)于幕後文化(huà)明(míng)貶暗褒的(de)情形,也(yě)就不足爲怪了(le)。
壬子(1972年)
南(nán)懷瑾先生講述
朱文光(guāng)記錄于台北(běi)
◎ 本文選編自東方出版社(簡體): 南(nán)懷瑾先生著《中國文化(huà)泛言(增訂本)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