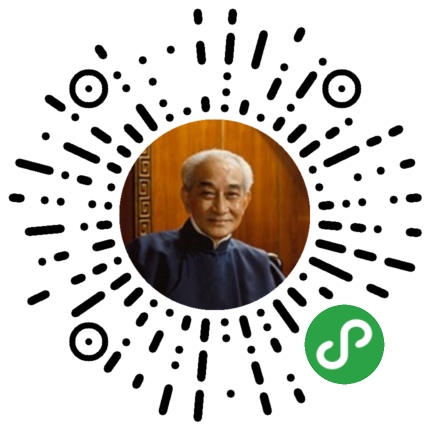南(nán)師文選
南(nán)懷瑾先生:《楞伽大(dà)義今釋》自叙
《楞伽》的(de)譯本,共有三種:
(1)宋譯(西元四四三年間劉宋時(shí)代):求那跋陀羅翻譯的(de)《楞伽阿跋多(duō)羅寶經》,計四卷。
(2)魏譯(西元五一三年間):菩提流支翻譯的(de)《入楞伽經》,計十卷。
(3)唐譯(西元七〇〇年間):實叉難陀翻譯的(de)《大(dà)乘入楞伽經》,計七卷。
普通(tōng)流行法本,都以宋譯爲準。
本經無論哪種翻譯,義理(lǐ)系統和(hé)文字結構,都難使人(rén)曉暢了(le)達。前人(rén)盡心竭力,想把高(gāo)深的(de)佛理(lǐ),譯成顯明(míng)章(zhāng)句,要使人(rén)普遍明(míng)白它的(de)真義,而結果愈讀愈難懂(dǒng),豈非背道而馳,有違初衷。有人(rén)說,佛法本身,固然高(gāo)深莫測,不可(kě)思議(yì),但譯文的(de)艱澀,讀之如對(duì)海上三山,可(kě)望而不可(kě)即,這(zhè)也(yě)是讀不懂(dǒng)《楞伽經》的(de)一個(gè)主要原因。其實,本經的(de)難通(tōng)之處,也(yě)不能完全歸咎于譯文的(de)晦澀,因爲《楞伽》奧義,本爲融通(tōng)性相之學,指示空有不異的(de)事理(lǐ),說明(míng)理(lǐ)論與修證的(de)實際,必須通(tōng)達因明(míng)(邏輯),善于分(fēn)别法相,精思入神,歸于第一義谛。同時(shí)要從真修實證入手,會之于心,然後方可(kě)探骊索珠,窺其堂奧。
無論中西文化(huà),時(shí)代愈向上推,所有聖哲的(de)遺教,大(dà)多(duō)是問答(dá)記錄,純用(yòng)語錄體裁,樸實無華,精深簡要。時(shí)代愈向後降,浮華愈盛,洋洋灑灑,美(měi)不勝收,實則有的(de)言中無物(wù),使人(rén)讀了(le)就想忘去爲快(kuài)。可(kě)是習(xí)慣于浮華的(de)人(rén),對(duì)于古典經籍,反而大(dà)笑(xiào)卻走,真是不笑(xiào)不足以爲道了(le)。《楞伽經》當然也(yě)是問答(dá)題材的(de)語錄體裁,粗看漫無頭緒,不知所雲,細究也(yě)是條分(fēn)縷析,自然有其規律,隻要将它先後次序把握得(de)住,就不難發現它的(de)系統分(fēn)明(míng),陳義高(gāo)深。不過,讀《楞伽》極需慎思明(míng)辨,嚴謹分(fēn)析,然後歸納論據,融會于心,才會了(le)解它的(de)頭緒,它可(kě)以說是一部佛法哲學化(huà)的(de)典籍(本經大(dà)義的(de)綱要,随手已列了(le)一張體系表)。他(tā)如《解深密》《楞嚴經》等,條理(lǐ)井然,層層轉進,使人(rén)有抽絲剝繭之趣,可(kě)以說是佛法科學化(huà)的(de)典籍。《阿彌陀》《無量壽》《觀》及密乘等經,神變難思,莊嚴深邃,唯信可(kě)入,又可(kě)以說是佛法宗教化(huà)的(de)典籍。所以研究《楞伽》,勢須具備探索哲學、習(xí)慣思辨的(de)素養,才可(kě)望其涯岸。
《楞伽經》的(de)開始,首先由大(dà)慧大(dà)士随意發問,提出了(le)一百多(duō)個(gè)問題,其中有關于人(rén)生的(de)、宇宙的(de)、物(wù)理(lǐ)的(de)、人(rén)文的(de),如果就每一個(gè)題目發揮,可(kě)以作爲一部百科論文的(de)綜合典籍,并不隻限于佛學本身的(de)範圍。而且這(zhè)些問題,也(yě)都是古今中外,人(rén)人(rén)心目中的(de)疑問,不僅隻是佛家的(de)需求。倘使先看了(le)這(zhè)些問題,覺得(de)來(lái)勢洶湧,好像後面将大(dà)有熱(rè)鬧可(kě)瞧,誰知吾佛世尊,卻不随題作答(dá),信手一擱,反而直截了(le)當地說心、說性、說相,依然引向形而上的(de)第一義谛,所以難免有人(rén)認爲大(dà)有答(dá)非所問的(de)感覺。實則,本經的(de)宗旨,主要在于直指人(rén)生的(de)身心性命與宇宙萬象的(de)根本體性。自然物(wù)理(lǐ)的(de)也(yě)好、精神思想的(de)也(yě)好,不管哪一方面的(de)問題,都基于人(rén)們面對(duì)現實世界,因現象的(de)感覺或觀察而來(lái),這(zhè)就是佛法所謂的(de)相。要是循名辨相,萬彙紛纭,畢竟永無止境。即使分(fēn)析到最後的(de)止境,或爲物(wù)理(lǐ)的(de),或爲精神的(de),必然會歸根結柢,反求之于形而上萬物(wù)的(de)本來(lái)而後可(kě)。因此吾佛世尊才由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識、二無我,加以析辨,指出一個(gè)心物(wù)實際的(de)“如來(lái)藏識”作爲總答(dá),此所以本經爲後世法相學者視爲唯識宗寶典的(de)原因。
自佛滅以後,唯識法相之學,随時(shí)代的(de)推進而昌明(míng)鼎盛,佛法大(dà)小乘的(de)經論,也(yě)可(kě)以純從唯識觀點而概括它的(de)體系。不幸遠(yuǎn)自印度,近及中國,乃至東方其他(tā)轉譯各國的(de)佛學,卻因此而有“勝義有”與“畢竟空”的(de)學術異同的(de)争論,曆兩千餘年不衰,這(zhè)誠非釋迦當初所樂(yuè)聞的(de)。殊不知“如來(lái)藏識”,轉成本來(lái)淨相,便更名爲“真如”,由薰習(xí)種性,便名爲“如來(lái)藏”,此中畢竟無我,非物(wù)非心,何嘗一定說爲勝義之有呢(ne)?所以在《解深密經》中,佛便說:“阿陀那識甚深細,一切種子如瀑流。我于凡愚不開演,恐彼分(fēn)别執爲我。”同一道理(lǐ),佛說般若方面,一切法如夢如幻,無去無來(lái),而性空無相,又真實不虛,他(tā)又何嘗定說爲畢竟的(de)空呢(ne)?倘肯再深一層體認修證,可(kě)謂法相唯識的(de)說法,卻是破相破執,才是徹底說空的(de)佛法。般若的(de)說法,倒是老實稱性而談,指示一個(gè)如來(lái)自性,躍然欲出呢(ne)!
但無論如何說法,佛法的(de)說心說性,說有說空,乃至說一真如自性,或非真如自性,它所指形而上的(de)體性,如何統攝心物(wù)兩面的(de)萬有群象?乃至形而上與形而下(xià)物(wù)理(lǐ)世界的(de)關聯樞紐,始終沒有具體的(de)實說;而且到底是偏向于唯心唯識的(de)理(lǐ)論爲多(duō),這(zhè)也(yě)是使人(rén)不無遺憾的(de)事。如果在這(zhè)個(gè)問題的(de)關鍵上,進一步剖析得(de)更明(míng)白,那麽,後世以至現代的(de)唯心唯物(wù)哲學觀點的(de)争辯,應該已無必要,可(kě)以免除世界人(rén)類一個(gè)長(cháng)期的(de)浩劫,這(zhè)豈不是人(rén)文思想的(de)一件大(dà)事嗎?唐代玄奘法師曾經著《八識規矩頌》,歸納阿賴耶識的(de)内義,說它“受熏持種根身器,去後來(lái)先做(zuò)主公”。而一般佛學,除了(le)注重在根身和(hé)“去後來(lái)先做(zuò)主公”的(de)尋討(tǎo)以外,絕少向器世界(物(wù)理(lǐ)世界)的(de)關系上,肯做(zuò)有系統而追根究柢的(de)研究,所以佛法在現代哲學和(hé)科學上,不能發揮更大(dà)的(de)光(guāng)芒。也(yě)可(kě)說是抛棄自家寶藏不顧,缺乏科學和(hé)哲學的(de)素養,沒有把大(dà)小乘所有經論中的(de)真義貫串起來(lái),非常可(kě)惜。如果稍能擺脫一些濃厚而無謂的(de)宗教習(xí)氣,多(duō)向這(zhè)一面著(zhe)眼,那對(duì)于現實的(de)人(rén)間世和(hé)将來(lái)的(de)世界,可(kě)能貢獻更大(dà)。我想,這(zhè)應該是合于佛心,當會得(de)到吾佛世尊的(de)會心微笑(xiào)吧!倘使要想向這(zhè)個(gè)方向研究,那對(duì)于《華嚴經》與《瑜伽師地論》等,有關于心識如何建立而形成這(zhè)個(gè)世界的(de)道理(lǐ),應該多(duō)多(duō)努力尋探,便會不負所望的(de)。
反之,說到參禅直求修證的(de)人(rén),最容易犯的(de)毛病,就是通(tōng)宗不通(tōng)教,于是許多(duō)在意根下(xià)立定足根,或在獨影(yǐng)境上依他(tā)起用(yòng),就相随境界而轉;或著(zhe)清靜、空無;或認光(guāng)明(míng)、爾焰;或樂(yuè)機辯縱橫;或死守古人(rén)言句。殊不知參禅,也(yě)僅是佛法求證的(de)初學入門方法,不必故自鳴高(gāo),不肯印證教理(lǐ),得(de)少爲足,便以爲是。這(zhè)同一般淺見誤解唯識學說者,認爲“諸法無自性”、或“一切無自性”,自己未加修證體認,便說禅宗的(de)明(míng)心見性是邪說,都同樣犯了(le)莫大(dà)的(de)錯誤。須知“諸法無自性”、“一切無自性”,這(zhè)個(gè)觀念,是指宇宙萬有的(de)現象界中,一切形器群象,或心理(lǐ)思想分(fēn)别所生的(de)種種知見,都沒有一個(gè)固定自存,或永恒不變的(de)獨立自性。這(zhè)些一切萬象,統統是如來(lái)藏中的(de)變相而已,所以說它“無自性”。《華嚴經》所謂“一切皆從法界流,一切還(hái)歸于法界”,便是這(zhè)個(gè)意思。如有人(rén)對(duì)法相唯識的(de)著作或說法,已經有此誤解者,不妨酌加修正,以免堕在自誤誤人(rén)、錯解佛法的(de)過失中,我當在此合掌曲躬,殷勤勸請。
一九六〇年,月(yuè)到中秋分(fēn)外明(míng)的(de)時(shí)候,《楞嚴大(dà)義》的(de)譯述和(hé)出版,初次告一段落,又興起想要著述《楞伽大(dà)義》的(de)念頭。有一天,在北(běi)投奇岩精舍講述《華嚴》會上,楊管北(běi)居士也(yě)提出這(zhè)個(gè)建議(yì),而且他(tā)的(de)夫人(rén)方菊仙女(nǚ)士,發心購(gòu)贈兩支上等鋼筆,回向般若成就。因緣湊泊,就一鼓作氣,從事本書(shū)的(de)譯述。自庚子重陽後開始,曆冬徂春,謹慎研思,不間寒暑晝夜,直到一九六一年六月(yuè)十二日,夏曆歲次辛醜四月(yuè)廿九日之夜,粗完初稿。在這(zhè)七八個(gè)月(yuè)著述的(de)過程中,覃思精研,有難通(tōng)未妥的(de)地方,唯有冥坐(zuò)入寂,求證于實際理(lǐ)地,而得(de)融會貫通(tōng)。那時(shí)我正寓居一個(gè)菜市場(chǎng)中,環境愦鬧,腥臊污穢堆積,在五濁陋室的(de)環境裏,做(zuò)此佛事,其中況味,憶之令人(rén)啞然失笑(xiào)!處于這(zhè)種情景十多(duō)年來(lái),已能習(xí)慣成自然,而沒有淨穢的(de)揀别了(le)。隻有一次冬夜揮毫,感觸正法陵夷、邪見充斥、人(rén)心陷溺的(de)現況,卻情不自禁,感作絕句四首,題爲《庚子冬夜譯經即賦》,雖如幻夢空花,姑錄之以爲紀念。
其一
風雨(yǔ)漫天歲又除,
泥塗曳尾說三車。
崖巉未許空生坐(zuò),
輸與能仁自著書(shū)。
其二
靈鹫風高(gāo)夢裏尋,
傳燈獨自度金針。
依稀昔日祇園會,
猶是今宵弄墨心。
其三
無著天親去未來(lái),
眼前兜率路崔嵬。
人(rén)間論議(yì)與誰證,
稽首靈山意已摧。
其四
青山入夢照(zhào)平湖,
外我爲誰傾此壺。
徹夜翻經忘已曉,
不知霜雪(xuě)上頭顱。
本書(shū)的(de)著述,參考《楞伽》三種原譯本,而仍以流通(tōng)本的(de)《楞伽阿跋多(duō)羅寶經》爲據,但譯義取裁,則彼此互采其長(cháng),以求信達。遇有覺得(de)需加申述之處,便随筆自加附論标記,說明(míng)個(gè)人(rén)的(de)見解,表示隻向自己負責而已。後來(lái)有人(rén)要求多(duō)加些附論,實在再提不起精神了(le)。這(zhè)次述著,除了(le)楊管北(běi)居士夫婦的(de)發心外,還(hái)有若幹人(rén)的(de)出力,他(tā)們的(de)發心功德,不可(kě)泯滅。台大(dà)農化(huà)系講師朱文光(guāng),購(gòu)贈稿紙千張,而且負責謄清和(hé)校對(duì),查訂附加注解,奔走工作,任勞任怨。雖然他(tā)向來(lái)緘默無聞,不違如愚,但這(zhè)多(duō)年來(lái),旦夕相處,從來(lái)不因我的(de)過于嚴格而引生退意,甚之,他(tā)做(zuò)了(le)許多(duō)功德事,也(yě)是爲善無近名的(de)。但到本經出版時(shí),他(tā)已留學美(měi)國,來(lái)信還(hái)自謂惜未盡力。其餘如師大(dà)學生陳美(měi)智、湯珊先,都曾爲謄稿抄寫出過力。中國文化(huà)研究所的(de)研究生吳怡,也(yě)曾爲本書(shū)參加過潤文和(hé)提出質疑的(de)工作。韓長(cháng)沂居士負責出版總校對(duì)。最後,程滄波居士爲之作序。這(zhè)些都是和(hé)本書(shū)著述完成及出版,有直接關系的(de)人(rén)和(hé)事,故記叙真相,作爲雪(xuě)泥鴻爪的(de)前塵留影(yǐng)。
本書(shū)述著完成以後,對(duì)于文字因緣,淡到索然無味,也(yě)許是俱生禀賦中的(de)舊(jiù)病,素來(lái)作爲,但憑興趣,興盡即中途而廢,不顧任何诟責,或者因人(rén)過中年,閱曆愈深,遇事反易衰退,故原稿抄好一擱,首尾又是四年了(le)。在這(zhè)四年中間,也(yě)寫作過儒、道兩家的(de)一些學術著作,但都是時(shí)作時(shí)辍,興趣索然。甚之覺得(de)著述都是多(duō)餘的(de)事,反而後悔以前動筆的(de)孟浪。每念德山禅師說的(de):“窮諸玄辯,若一毫置于太虛。竭世樞機,似一滴投于巨壑。”實在是至理(lǐ)名言,很想自己毀之爲快(kuài)。引用(yòng)佛家語來(lái)說,可(kě)謂小乘之念,随時(shí)油然而生。故對(duì)本書(shū)的(de)出版,一延再延。今年春正,禅集法會方畢,楊管北(běi)居士又提出此事,并且說,爲回向他(tā)先慈薛太夫人(rén),要獨自捐資印刷本書(shū)五千部,贈送結緣,藉資冥福,所以今日才有本書(shū)的(de)問世。始終成其事者,爲楊管北(běi)居士。經雲:“孝子不匮,永錫爾類。”我但任興而爲,得(de)失是非,都了(le)不相涉,隻是對(duì)本書(shū)的(de)譯文,仍然不如理(lǐ)想的(de)暢達,确很遺憾。倘使将來(lái)觸動修整的(de)興趣,再爲本書(shū)未能盡善的(de)缺憾處,重做(zuò)一番補過工夫。但排印中間,又爲誤罹目疾而耽擱了(le)七八個(gè)月(yuè),深感業重障深,蒇事之難。本來(lái)要替本經與唯識法相的(de)關系,及性相兩宗的(de)互通(tōng)之處,作一篇簡單的(de)綱要,但又覺得(de)多(duō)事著述,徒費筆墨紙張,于人(rén)于世,畢竟沒有多(duō)大(dà)益處,所以便懶得(de)提筆。唯在前賢著述中,尋出範古農居士述《八識規矩頌貫珠解》,附印于次,以便學者對(duì)唯識法相,有一基本認識,可(kě)以由此入門,研究性相的(de)異同,契入經藏。
(西元一九六五年,台北(běi))
◎ 本文選編自東方出版社(簡體): 南(nán)懷瑾先生著《中國文化(huà)泛言(增訂本)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