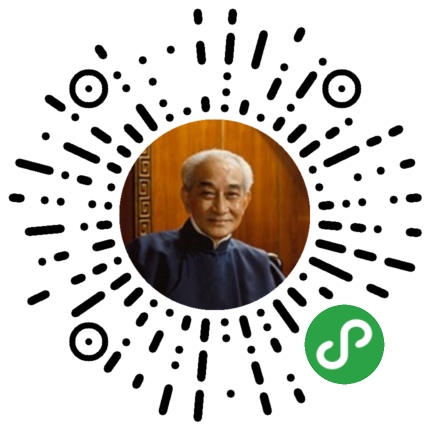南(nán)師文選
南(nán)懷瑾先生:宋明(míng)理(lǐ)學與禅宗
提到曆史文化(huà)的(de)演變與發展,我們可(kě)以再用(yòng)一個(gè)新的(de)觀念來(lái)說,在人(rén)類曆史文化(huà)的(de)發展過程中,有兩個(gè)非常尖銳對(duì)比的(de)事實,它始終存在于曆史的(de)現實之中。
(一)爲人(rén)盡皆知的(de)曆史上治權的(de)事實,包括古今中外曆代帝王的(de)治權,這(zhè)是一般人(rén)所謂的(de)大(dà)業。
(二)爲學術思想的(de)威權,它雖然不像曆史上帝王治權那樣有赫赫事功的(de)寶座,但是它卻在無形之中領導了(le)古今中外曆史的(de)趨向,而非帝王将相之所能爲。過去中國的(de)文化(huà)界,尊稱孔子爲“素王”,也(yě)便是内涵有這(zhè)個(gè)觀念。這(zhè)是千秋大(dà)業,也(yě)許當人(rén)有生之年,卻是長(cháng)久的(de)寂寞凄涼,甚之是非常悲慘的(de),可(kě)是它在無形之中,卻左右領導了(le)曆史的(de)一切,而且它有永久的(de)威權和(hé)長(cháng)存的(de)價值。
前者在莊子與孟子的(de)共同觀念中,應該稱之謂“人(rén)爵”;後者稱之謂“天爵”。而且我們借用(yòng)孟子的(de)“五百年必有王者興,其間必有名世者”的(de)兩句話(huà)來(lái)講,在人(rén)類曆史文化(huà)發展史上,的(de)确若合符節,并非虛語。因此,我們在前面說過,姑且借用(yòng)西曆紀元作标準,以五百年作一階段,簡要地說明(míng)本題的(de)内涵。
壹、從曆史分(fēn)判中國文化(huà)思想的(de)大(dà)勢
(一)周代文化(huà)——文武周公階段
本題爲了(le)針對(duì)儒家學術思想的(de)趨勢來(lái)說,因此斷自周代文化(huà)開始,換言之,第一個(gè)五百年間,便要從周公的(de)學術思想開始(約當西元前一一一五至一〇七九年間)。因爲孔子的(de)學術思想,是“祖述堯舜,憲章(zhāng)文武”,而且也(yě)自認爲随時(shí)在夢見周公,推崇“郁郁乎文哉”的(de)周代文化(huà),是集中國上古以來(lái)文化(huà)的(de)大(dà)成。
(二)孔孟思想的(de)階段
第二個(gè)五百年,約始自西元前五七一至五四五年間,才是孔孟思想興起的(de)階段。孔子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(西元前五五一年)。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(西元前三七二年)。由此而經六國到秦、漢時(shí)期(西元前二五五至二〇二)。孔孟與儒家的(de)學術思想,雖然崛立于魯衛之間,但當此時(shí)期諸子百家的(de)學術思想普遍流行,道、墨、名、法、縱橫、陰陽等家,彌漫朝野,它們被諸侯之間所接受和(hé)歡迎,還(hái)勝于孔孟思想。即如漢初統一天下(xià),從文景開始,也(yě)是重用(yòng)道家的(de)黃(huáng)老思想。一直到西元前一四〇年間,由漢武帝開始重視儒術,再經公孫弘、董仲舒等的(de)影(yǐng)響,因此而“罷黜百家,一尊于儒”。孔子的(de)學術思想,和(hé)董仲舒等所代表的(de)儒家思想,才從此而正式建立它的(de)學術地位。這(zhè)也(yě)正是司馬遷所說“自周公卒,五百歲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,有能紹明(míng)世,正易傳,繼春秋,本詩、書(shū)、禮、樂(yuè)之際,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讓焉”的(de)階段。但在西漢這(zhè)一階段的(de)儒家學術思想,著(zhe)重在記誦辭章(zhāng)與訓诂之學,并無性命的(de)微言與道統問題的(de)存在。而且當時(shí)的(de)代表大(dà)儒董仲舒,他(tā)是集陰陽、道家思想的(de)儒學,也(yě)可(kě)以說是外示儒術、内啓陰陽谶緯之學先聲的(de)儒學。至于公孫弘等見之于從政的(de)儒行,幾近“鄉願”,遠(yuǎn)非孔孟的(de)精神,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上列述公孫弘的(de)史事,備有微言,不及細述。
(三)儒、道、佛文化(huà)思想的(de)交變階段
到了(le)第三個(gè)五百年,正當西曆紀元開始,也(yě)正是新莽篡位到東漢的(de)時(shí)期(王莽于西元九年正式篡位。而且揚雄所著《太玄》的(de)術數之學,另啓東漢陰陽術數的(de)儒學思想之漸)。由此經漢末到三國之間,也(yě)正是儒家經學的(de)注疏集成階段,将近三百年來(lái)兩漢的(de)儒學,到此已近于尾聲。代之而起的(de),便是中國文化(huà)史上有名的(de)“三玄”——《易經》《老子》《莊子》之學的(de)擡頭。從此曆魏、晉、南(nán)北(běi)朝而到梁武帝的(de)階段,便是佛教禅宗的(de)初祖——達摩大(dà)師東來(lái)的(de)時(shí)期(梁武帝自西元五〇三年建國,達摩大(dà)師的(de)東來(lái),約當西元五一三年間的(de)事)。我們必須注意王莽的(de)思想,也(yě)是承受儒家政治思想的(de)一脈,以恢複井田制度的(de)理(lǐ)想爲目的(de)。但他(tā)缺乏心性修養之學的(de)造詣,與孔、孟的(de)儒學思想無關。
在這(zhè)第三個(gè)五百年間,自漢末三國之際,由于佛教傳入之後,儒、佛、道三家的(de)優劣,和(hé)宗教哲學的(de)争論,以及有神(非宗教之神的(de)觀念)與無神之辯,一直延續到隋唐之際。有關這(zhè)些文獻的(de)資料,我們都保留得(de)很多(duō),可(kě)惜注意它的(de)人(rén)并不太多(duō)。因此可(kě)說這(zhè)個(gè)時(shí)期,是儒、道、佛文化(huà)思想的(de)交變階段。
其次佛教的(de)各宗,也(yě)在此階段開始逐漸萌芽。例如與禅宗并重的(de)天台宗,也(yě)自梁天監十三年到唐貞觀年間正式形成。負有盛名的(de)天台宗智者大(dà)師,便在隋開皇十七年間才開張他(tā)的(de)大(dà)業。
如果以儒家學術爲主的(de)立場(chǎng)來(lái)講,這(zhè)五百年間可(kě)以說是儒學的(de)衰落時(shí)期。
(四)隋、唐文化(huà)與儒、道、佛及理(lǐ)學勃興的(de)階段
第四個(gè)五百年,便是隋、唐文化(huà)到宋代理(lǐ)學興起的(de)階段。中國佛教十宗與中國佛學體系的(de)建立确定,便是由隋到初唐而至于天寶年間的(de)事(約當西元六〇〇至七五六年間)。但這(zhè)個(gè)階段,卻是中國文化(huà)最光(guāng)榮的(de)階段,也(yě)可(kě)以說是唐代文化(huà)鼎盛的(de)階段,可(kě)是儒家的(de)學術思想,除了(le)詞章(zhāng)記誦以外,并無太多(duō)義理(lǐ)的(de)精微。其中最值得(de)一提的(de):
(1)便是文中子融會儒、道、佛的(de)學術,影(yǐng)響領導初唐建國的(de)思想頗大(dà)。
(2)其次,便是孔穎達有關儒學注疏的(de)撰解,以及天寶年間李鼎祚《易經集解》的(de)完成,都對(duì)漢儒之學有其集成的(de)功勞。
禅宗的(de)興盛:但自唐太宗貞觀之後,從達摩大(dà)師傳來(lái)一系的(de)禅宗,南(nán)能(在南(nán)方的(de)六祖慧能)和(hé)北(běi)秀(在北(běi)方的(de)神秀)之後嗣,便大(dà)闡宗風,風靡有唐一代。我們如果強調一點說初唐的(de)文化(huà),便是禅的(de)文化(huà),也(yě)并不爲過。但在此時(shí)期,道教正式建立,道家和(hé)道教的(de)學術思想,自貞觀以後,也(yě)同禅宗一樣,同樣地具有極大(dà)的(de)影(yǐng)響力。因爲佛教受到禅宗影(yǐng)響而普遍地宏開,于是引起中唐以後,中國文化(huà)史上有名的(de)韓愈辟佛事件。
韓愈辟佛開啓宋儒理(lǐ)學的(de)先聲:韓愈辟佛事件及其著作《原性》《原道》和(hé)《師說》的(de)名文,是在唐憲宗元和(hé)間(約當西元八一九年)的(de)事。我們說句平實的(de)話(huà),隻要仔細研究韓愈的(de)思想和(hé)當時(shí)文化(huà)與宗教的(de)情形,與其說韓愈是在辟佛,毋甯說韓愈是在排僧,或者可(kě)以說在激烈地排斥佛教的(de)形式而已。至于韓愈在《原道》中所提出“博愛(ài)之謂仁”的(de)思想,那是從他(tā)專門研究墨子思想的(de)心得(de),融化(huà)入于儒家思想之中。一般人(rén)都忘了(le)韓愈的(de)學問,緻力最深的(de)是墨學,因爲後世很多(duō)人(rén)忘記了(le)這(zhè)個(gè)重點,便人(rén)雲亦雲,積重難返了(le)。其實,除了(le)韓愈的(de)辟佛,漸啓後來(lái)宋儒理(lǐ)學的(de)先聲之外,真正開啓宋儒理(lǐ)學思想的(de)關鍵,應該是與韓愈有師友關系的(de)李翺所著之《複性書(shū)》一文。
禅宗五家宗派的(de)隆盛:由大(dà)曆、大(dà)中(西元七七〇至八五三年)到元和(hé)、鹹通(tōng)、開成、天複(西元八三九至九〇一年)乃至五代周顯德(西元八八四至九五六年)之間。禅宗的(de)五家宗派,鼎峙崛起,各自建立門庭,互闡禅宗。如沩仰宗所建立〇圓相的(de)旨趣,開啓宋代“太極圖”的(de)先河(hé)。曹洞宗的(de)五位君臣,取《易經》重離之卦的(de)互疊作用(yòng),激發宋代邵康節的(de)易學思想。臨濟宗的(de)“三玄三要”之旨,對(duì)宋儒理(lǐ)學的(de)“太極涵三”之旨趣,極有影(yǐng)響。
此外,雲門宗和(hé)法眼宗的(de)說法,也(yě)都與理(lǐ)學有息息相關之妙。
(五)宋儒的(de)理(lǐ)學階段
第五個(gè)五百年,便是繼晚唐五代以後宋代儒家理(lǐ)學的(de)興起。宋太祖的(de)建國,正當西元九六〇年間的(de)事。到了(le)乾德五年(西元九六七年)便有中國文化(huà)史上有名的(de)“五星聚奎”的(de)記事。這(zhè)個(gè)天文星象的(de)變象,也(yě)就是後世一般人(rén)認爲是感應宋初“文運當興”的(de)象征。因此認爲宋初産生了(le)理(lǐ)學的(de)五大(dà)儒,就是“五星聚奎”的(de)天象應運而生的(de)。
到了(le)宋仁宗景德年間(約當西元一〇〇〇年間),儒家的(de)理(lǐ)學大(dà)行,已有要取禅宗而代之的(de)趨勢。但在此之先由宋真宗開始,道教也(yě)大(dà)爲流行,一直影(yǐng)響了(le)徽、欽北(běi)狩和(hé)高(gāo)宗南(nán)渡的(de)局面。在此同時(shí)可(kě)以注意的(de),便是西元一〇六八年間,宋神宗起用(yòng)王安石,又想要恢複井田制度等的(de)理(lǐ)想,因此宋代的(de)黨禍和(hé)理(lǐ)學門戶之争,便也(yě)在此時(shí)期揭開了(le)序幕,這(zhè)是中國文化(huà)學術史上一件非常遺憾,也(yě)許可(kě)以說是一件很有趣的(de)史事。
可(kě)是在當此之前五百年間,禅宗的(de)王氣将衰,到了(le)這(zhè)個(gè)五百年間,宋代五大(dà)儒的(de)理(lǐ)學思想,崛然興起而替代了(le)禅宗五家宗派的(de)盛勢,雖曰人(rén)事,豈非天命哉!
(六)明(míng)代理(lǐ)學與王學的(de)階段
第六個(gè)五百年,就是由宋儒朱熹、陸象山開始,經曆元、明(míng)而到王陽明(míng)理(lǐ)學的(de)權威時(shí)期。朱熹生在建炎四年(西元一一三〇年),卒于慶元六年(西元一二〇〇年)。陸象山生于紹興九年(西元一一三九年),卒于紹熙三年(西元一一九二年)。朱熹的(de)“道問學”和(hé)“集義之所生”的(de)宗旨,和(hé)陸象山的(de)“尊德性”而直指心性,不重支離瑣碎的(de)探索,便是中國文化(huà)史上非常有名的(de)朱、陸思想異同之争的(de)一重學案。到了(le)明(míng)代憲宗成化(huà)和(hé)嘉靖之間(約當西元一四七二至一五二八年間),王陽明(míng)理(lǐ)學的(de)思想大(dà)行,從此以後,中國文化(huà)思想的(de)領域,大(dà)半都是陸、王的(de)思想。
由此經明(míng)武宗而到萬曆,王學大(dà)行,末流所及,弊漏百出,終至有“聖人(rén)滿街(jiē)走,賢人(rén)多(duō)于狗”之譏。理(lǐ)學到此,已勢成強弩之末,也(yě)與禅宗一樣,都有等分(fēn)齊衰之慨了(le)。
(七)清代經學與理(lǐ)學的(de)階段
第七個(gè)五百年,就是清初諸大(dà)儒,如顧炎武、黃(huáng)梨洲、顧習(xí)齋、李二曲等人(rén),遭遇國亡家破之痛,鑒于明(míng)末諸儒“平時(shí)靜坐(zuò)談心性,臨危一死報君王”的(de)迂疏空闊,大(dà)唱樸學務實,學以緻用(yòng)于事功的(de)成就。一變明(míng)末理(lǐ)學的(de)偏差,大(dà)有宋儒陳同甫、辛棄疾的(de)風範。而且極力鼓吹民族正氣的(de)良知,延續中華民族的(de)正氣和(hé)中國文化(huà)的(de)精神,因此影(yǐng)響直到清末而産生了(le)國父孫先生的(de)思想,如《建國方略》和(hé)《心理(lǐ)建設》等等,也(yě)可(kě)以說是承接顧炎武、黃(huáng)梨洲之後而繼孔、孟儒家思想,融會古今中外的(de)文化(huà)學術而構成簡明(míng)易曉的(de)大(dà)成。
由清兵(bīng)入關而到甲申建國的(de)時(shí)期,也(yě)便是西元一六四四年間的(de)事,從此自十九世紀的(de)末期而到現在的(de)二十世紀,我們的(de)學術思想和(hé)曆史文化(huà),又遭遇一個(gè)古今中外未有的(de)巨變階段。理(lǐ)學的(de)形式和(hé)禅宗的(de)新姿态,似乎正在複活,它将與古今中外的(de)洪流,有接流融會的(de)趨勢。衡之曆史的(de)先例,以及《易經》術數之學的(de)證驗,很快(kuài)的(de)将來(lái),新的(de)中國文化(huà)的(de)精神,必将又要重現于世界了(le)。孟子說:“五百年必有王者興,其間必有名世者,由周以來(lái),五百有餘歲矣。以其數,則過矣,以其時(shí)考之則可(kě)矣。”我們這(zhè)一代的(de)青少年們,真需要發心立志,記住張橫渠的(de)“爲天地立心,爲生民立命,爲往聖繼絕學,爲萬世開太平”的(de)名訓,作爲國家、爲自己事業前途的(de)準繩。
貳、理(lǐ)學與禅宗的(de)關系
我們已就曆史的(de)觀念,分(fēn)判中國文化(huà)思想的(de)大(dà)勢,有關禅宗與理(lǐ)學興起的(de)大(dà)概,便可(kě)由此而了(le)然于心。至于理(lǐ)學與禅宗學術思想交互演變的(de)詳情,實非片言可(kě)盡,現在僅就其要點,稍作簡介,提供研究者參考之一得(de),其間的(de)是非得(de)失,則各有觀點的(de)不同,“道并行而不悖”,要亦無傷大(dà)雅也(yě)。
(一)理(lǐ)學名詞的(de)問題
宋儒的(de)理(lǐ)學,原本隻是遠(yuǎn)紹孔、孟、荀子以來(lái)儒家的(de)學術思想,起初并無專以“理(lǐ)”字作爲特定的(de)名詞。自周濂溪以下(xià),講學的(de)方式,已經一變“性與天命,夫子罕言”的(de)風格,動辄便以天人(rén)之際的(de)“宇宙”觀與形而上的(de)“道體論”作根據,由此而建立一個(gè)人(rén)生哲學的(de)新體系。濂溪以次,以“理(lǐ)氣”、“理(lǐ)欲”等新的(de)名詞,用(yòng)作心性之理(lǐ)的(de)整體的(de)發揮,因此後世便以宋儒的(de)儒學,别稱謂“性理(lǐ)學”,簡稱叫作“理(lǐ)學”。《宋史》對(duì)此,又别創體裁,特在《儒林(lín)傳》之外,又另立《道學傳》的(de)一格,專門收羅純粹的(de)“理(lǐ)學家”,以有别于“儒林(lín)”。其實,無論周、秦以來(lái)的(de)儒家,以及孔、孟的(de)學術思想,并無特别提出以“理(lǐ)”馭“氣”,或“理(lǐ)氣”二元并論,同時(shí)亦無以“天理(lǐ)”與“人(rén)欲”等等規定嚴格界别的(de)說法。至于根據《說卦傳》的(de)文言,以“窮理(lǐ)盡性而至于命”的(de)“理(lǐ)”字作根據,确定“理(lǐ)學”家們“理(lǐ)”即“性”、“理(lǐ)”即“天”的(de)定論,那是有問題的(de)。況且《說卦傳》是否爲孔子所作的(de)可(kě)靠性,也(yě)正爲後世所懷疑,事非本題的(de)要點,所以姑且略而不論。
在中國文化(huà)思想的(de)領域裏,正式以“理(lǐ)”字作爲入道之門的(de),首先應從南(nán)朝梁武帝時(shí)期,禅宗初祖達摩大(dà)師所提出的(de)“理(lǐ)入”與“行入”開始,從此而有隋、唐之間,佛學天台宗與華嚴宗的(de)分(fēn)科判教,特别提出修學佛法的(de)四階段,從“聞、思、修、慧”而證“教、理(lǐ)、行、果”以契合于“信、解、行、證”的(de)要點,因此而有特别重視“窮理(lǐ)盡性”的(de)趨向,由教理(lǐ)的(de)“觀行”而契證“中觀”的(de)極則(包括形而上的(de)本體論與形而下(xià)的(de)形器世間——即由宇宙論而到人(rén)生哲學)的(de)涵義,确立爲事法界(形器與人(rén)物(wù)之間)、理(lǐ)法界(理(lǐ)念與精神之際)、事理(lǐ)無礙法界、事事無礙法界的(de)“四法界”觀念,應爲開啓宋儒契理(lǐ)契機的(de)強有力之影(yǐng)響。關于華嚴“四法界”之說,但讀唐代澄觀法師、圭峰法師、李長(cháng)者等的(de)巨著可(kě)知,恕不詳及。
但華嚴宗的(de)大(dà)師,如澄觀、圭峰等,都是初遊禅宗之門而有所得(de),從此宏揚教理(lǐ),特别提倡華嚴思想體系的(de)建立,融會禅理(lǐ)與華嚴教理(lǐ)的(de)溝通(tōng)。因此互相影(yǐng)響,到了(le)中唐以後,如創立沩仰宗的(de)沩山大(dà)師,提倡“實際理(lǐ)地(對(duì)心性與宇宙貫通(tōng)的(de)形而上本體的(de)特稱),不著(zhe)一塵。萬行門中(指人(rén)生的(de)行爲心理(lǐ)與道德哲學),不舍一法”的(de)名言,特别強調“理(lǐ)地”作爲心性本際的(de)标旨。從此“實際理(lǐ)地”的(de)話(huà)頭,便流傳于禅宗與儒林(lín)之間,極爲普遍。
綜合以上所講自梁武帝時(shí)代,達摩大(dà)師提出“理(lǐ)入”法門開始,和(hé)天台、華嚴等宗對(duì)于“理(lǐ)”的(de)觀念之建立,以及沩山禅師提倡“實際理(lǐ)地”的(de)名言之後,先後經過五百年間的(de)互相激蕩,因此而形成宋儒以“理(lǐ)”說性的(de)種種思想,便成爲順理(lǐ)成章(zhāng)的(de)事實了(le)。其間學術思想的(de)演變與發展,以及互受影(yǐng)響的(de)種種詳實,已可(kě)由此一斑,而得(de)窺全豹了(le)。
其次,在唐憲宗大(dà)曆、大(dà)中迄開成、天複之間,沩山、仰山師徒所建立的(de)禅門,以九十六圓相綱宗(包括圓相、暗機、義海、字海、意語、默論等六重意義);洞山、曹山師徒以重離(上☲下(xià)☲)卦而立五位君臣的(de)宗旨。因此演變發展而逐漸啓發周濂溪的(de)《太極圖說》,與邵康節易理(lǐ)象數的(de)哲學思想,都有極其密切的(de)關系和(hé)迹象可(kě)尋。但因涉及文化(huà)思想史的(de)考證範圍,又非片言可(kě)盡,現在隻能舉其簡略,以資參考而已。至于沩、仰與曹、洞師徒的(de)〇圓相與重離思想的(de)來(lái)源,則又自挹注《易經》與道家的(de)觀念而注釋禅修的(de)方法,那又别是一個(gè)問題,以後另行討(tǎo)論可(kě)也(yě)。
(二)周濂溪遊心禅道的(de)資料
相傳周茂叔曾經從學于潤州(江蘇鎮江)鴻林(lín)寺僧壽涯,參禅于黃(huáng)龍(山名)慧南(nán)禅師及晦堂祖心禅師。又嘗拜谒廬山歸宗寺之佛印了(le)元禅師,師事東林(lín)寺僧常聰。釋感山所著《雲卧紀談》謂:“周子居廬山時(shí),追慕往古白蓮社(晉代淨土宗初祖慧遠(yuǎn)法師所創立)故事,結青松社,以佛印爲主。”常聰門人(rén)所著《紀聞》謂:“周子與張子得(de)常聰‘性理(lǐ)論’及‘太極、無極’之傳于東林(lín)寺。”又,周濂溪常自稱“窮禅客”,這(zhè)是見于遊定夫的(de)語錄中的(de)實話(huà)。至于他(tā)所作的(de)詩,經常提到與佛有緣的(de)事,并不如後代理(lǐ)學家們的(de)小氣,反而諱莫如深。例如《題大(dà)颠壁》雲:“退之自謂如夫子,原道深排佛老非。不識大(dà)颠何似者?數書(shū)珍重寄寒衣。”(因韓愈在潮州時(shí),曾三函大(dà)颠禅師。在袁州時(shí),曾布施二衣,故茂叔詩中特别提出此事)《宿山房(fáng)》雲:“久厭塵勞樂(yuè)靜玄,俸微猶乏買山錢。徘徊真境不能去,且寄雲房(fáng)一榻眠。”如《經古寺》雲:“是處塵埃皆可(kě)息,時(shí)清終未忍辭官。”至于周子的(de)《通(tōng)書(shū)》四十章(zhāng),揭發“誠”與“敬”之爲用(yòng),實與禅宗佛教誠笃敬信的(de)主旨,語異而實同,不必詳論。
(三)邵康節學術思想的(de)淵源與曹洞宗旨的(de)疑案
關于邵子的(de)學術思想,如果說是出于道家,這(zhè)是不易引起紛争的(de)事。倘使有人(rén)認爲他(tā)與禅宗有關,那麽可(kě)能就會引起嘩然訾議(yì)了(le)。但由多(duō)年來(lái)潛心研究邵子的(de)易象數之學與《皇極經世》的(de)《觀物(wù)》内外二篇的(de)思想,愈加确立此一信念。至少可(kě)說邵子對(duì)易學的(de)哲學觀念,實爲遠(yuǎn)紹禅、道兩家的(de)思想啓發而來(lái)。即如他(tā)所祖述的(de)陳抟本人(rén)的(de)思想,亦與禅宗具有密切的(de)關系。此事言之話(huà)長(cháng),今但就最簡要易曉的(de)略一說明(míng)而已。
今據大(dà)家手邊易找的(de)資料,如全祖望在《宋元學案》的(de)《叙錄》說:“康節之學,别爲一家。或謂《皇極經世》,隻是京、焦末流。然康節之可(kě)以列聖門者,正不在此。亦猶溫公之造九分(fēn)者,不在《潛虛》也(yě)。”黃(huáng)百家雲:“周、程、張、邵五子并時(shí)而生,又皆知交相好……而康節獨以圖書(shū)象數之學顯。考其初,先天卦圖,傳自陳抟;抟以授種放,放授穆修,修授李之才,之才以授先生。顧先生之教,雖受于之才,其學實本于自得(de)……蓋其心地虛明(míng),所以能推見得(de)天地萬物(wù)之理(lǐ)。即其前知,亦非術數之比。”據此以推,陳抟爲唐末五代間人(rén),陳抟之先,先天八卦圖,又得(de)授受于何人(rén)?唐以前無之,亦如理(lǐ)學家在唐以前并無此說,是一樣地截流橫斷而來(lái),豈非大(dà)有可(kě)疑者在也(yě)?如果推求于禅宗的(de)五家之中,曹洞師徒,便已開其倪端。雖然對(duì)邵子的(de)術數之學,略無牽涉,但陳抟與邵子的(de)易象數之學,與唐代的(de)一行禅師的(de)術數之學,都有關聯之處。根據易理(lǐ)象數而言宇宙人(rén)物(wù)生命之本元問題“道”(哲學)的(de)思想,與曹洞宗旨,卻極其“性相近也(yě),習(xí)相遠(yuǎn)也(yě)”。其中理(lǐ)趣,大(dà)有可(kě)觀,唯限于時(shí)間篇幅,僅略一提撕,提起研究者之注意而已。
曹洞宗據重離(上☲下(xià)☲)卦的(de)五位君臣說:五位乃洞山良價禅師所創,借易之卦爻而判修證之淺深(名爲功勳之五位,爲洞山之本意),示理(lǐ)事之交涉(名爲君臣之五位,爲曹山之發明(míng))。洞山禅師以“__”代表正也(yě)、體也(yě)、君也(yě)、空也(yě)、真也(yě)、理(lǐ)也(yě)、黑(hēi)也(yě),“_ _”代表偏也(yě)、用(yòng)也(yě)、臣也(yě)、色也(yě)、俗也(yě)、事也(yě)、白也(yě)。并取離(上☲下(xià)☲)卦回互卦變之而爲五位。其疊之次第:1.重離(上☲下(xià)☲)卦。2.中孚(上☴下(xià)☱)卦,取重離卦中之二爻加于上下(xià)。3.大(dà)過(上☱下(xià)☴)卦,取中孚卦中之二爻加于上下(xià)。4.巽(☴)卦,取單離,以其中爻回于下(xià)。5.兌(☱)卦,取單離,以其中爻回于上。
洞山禅師又由爻之形而圖黑(hēi)白之五位:1.巽(☴)卦君位。正中偏:正者體也(yě)、空也(yě)、理(lǐ)也(yě)。偏者用(yòng)也(yě)、色也(yě)、事也(yě)。正中之偏者,正位之體處,具偏用(yòng)事相之位也(yě)。是能具爲體,所具爲用(yòng),故以能具之體,定爲君位。學者始認體具之用(yòng),理(lǐ)中之事,作有爲修行之位,爲功勳五位之第一位。配于大(dà)乘之階位,則與地前三賢之位相當。2.兌(☱)卦臣位。偏中正:是偏位之用(yòng),具正位之體之位。因之以能具之用(yòng),定爲臣用(yòng),即君臣五位之臣位也(yě)。在修行上論之,則爲正認事具之理(lǐ),用(yòng)中之體,達于諸法皆空真如平等之理(lǐ)之位,即大(dà)乘之見道也(yě)。3.(上☱下(xià)☴)大(dà)過卦君視臣。正中來(lái):有爲之諸法如理(lǐ)随緣,如性緣起者,即君視臣之位。學者在此,如理(lǐ)修事,如性作行,是與法身菩薩由初地到七地之有功用(yòng)修道相當者。4.(上☴下(xià)☱)中孚卦臣向君。偏中至:事用(yòng)全契于體,歸于無爲者,即臣向君之位。學者于此終日修而離修念,終日用(yòng)而不見功用(yòng),即由八地至十地之無功用(yòng)修道位。5.(上☲下(xià)☲)重離卦君臣合。兼中到:是體用(yòng)兼到,事理(lǐ)并行者。即君臣合體之位,爲最上至極之佛果也(yě)。
以上就法而論,事理(lǐ)之回互,爲君臣之五位;就修行上而判淺深,爲功勳之五位。
上面僅就部分(fēn)的(de)研究資料而說,其他(tā)如洞山良價禅師因涉溪水(shuǐ)照(zhào)影(yǐng)而悟道的(de)偈語說:“切忌從他(tā)覓,迢迢與我疏。我今獨自往,處處得(de)逢渠。渠今正是我,我今不是渠。應須恁麽會,方得(de)契如如。”它與邵康節的(de)“冬至子之半,天心無改移。一陽初動處,萬物(wù)未生時(shí)”,以及邵子《觀物(wù)吟》“耳(☵)目(☲)聰明(míng)男(nán)子身,洪鈞賦與不爲貧。因探月(yuè)窟方知物(wù),未蹑天根豈識人(rén)。乾(☰)遇巽(☴)時(shí)觀月(yuè)窟,地(☷)逢雷(☳)處見天根。天根月(yuè)窟閑來(lái)往,三十六宮都是春”,其間的(de)思想脈絡互通(tōng)之處,實在是頗饒尋味。至于《皇極經世》書(shū)中,假設“元會運世”的(de)曆史哲學之觀念,與佛學“成住壞空”的(de)“劫運”、“劫數”之說,更有明(míng)顯的(de)關連。總之,邵子之學,發明(míng)禅道兩家的(de)學術思想之處甚多(duō),義屬專題,一時(shí)也(yě)恕難詳盡。
(四)張橫渠排斥佛老與佛道之因緣
與周濂溪、邵康節同時(shí)而稍後的(de)理(lǐ)學家,便有張載和(hé)二程——程颢、程頤。張橫渠少有大(dà)志,喜談兵(bīng)。嘗上書(shū)幹谒範仲淹。仲淹對(duì)他(tā)說:“儒者自有名教可(kě)樂(yuè),何事于兵(bīng)?”授以《中庸》。乃立志求學。初求之佛、老,後恍然曰:“吾道自足,何事旁求?”世傳橫渠之學,以“易”爲宗旨,以“中庸”爲目的(de),以禮爲體,以孔、孟爲極。但是橫渠的(de)任氣尚義,在氣質上,與孟子的(de)風格,更爲相近。
周濂溪的(de)學說,在“太極”之上,加一“無極”。其用(yòng)意,似乎爲調和(hé)儒家的(de)“太極”與道家的(de)“無極”。有人(rén)說濂溪“太極”的(de)涵義,猶如佛學的(de)“依言真如”;“無極”的(de)涵義,猶如佛學的(de)“離言真如”。但他(tā)說“無極”而“太極”,則又似佛說“性空緣起”,以及老子的(de)“有生于無”。
張橫渠隻說到“太極”,并不提“無極”。但他(tā)對(duì)于“太極”的(de)解釋,又不可(kě)說是“無”。而且他(tā)批評老子“有生于無”之說,以爲錯了(le),又是以“有”作根據的(de)。自語相違,互自矛盾之處甚多(duō)。這(zhè)是周、張二人(rén)思想的(de)根本不同之處。橫渠說出“氣”字,又提出性有“天地之性”與“氣質之性”的(de)不同。周濂溪對(duì)于佛教,很少有顯著排斥性的(de)批評。張橫渠的(de)著作中,排佛之言甚多(duō)。例如駁斥佛學“以山河(hé)大(dà)地爲見病,以六合爲塵芥,以人(rén)生爲幻妄,以有爲贅疣,以世爲蔭濁”,又說“彼語寂滅者,往而不反;徇生執有者,物(wù)而不化(huà)。二者雖有間矣,以言乎失道,則均焉”等等,大(dà)體都是粗讀《楞嚴經》的(de)“世界觀”、“人(rén)生觀”而立論,并未深知《華嚴》《涅槃》經等的(de)理(lǐ)趣。但他(tā)在《西銘》中,開示學者“民吾同胞,物(wù)吾與也(yě)”的(de)觀點,以及他(tā)平時(shí)告誡學者“爲天地立心,爲生民立命,爲往聖繼絕學,爲萬世開太平”等觀念,則又似佛學的(de)衆生平等,因此興起“同體之悲,無緣之慈”,以及視心佛衆生爲“正報”,山河(hé)大(dà)地爲“依報”之說的(de)啓發交變而來(lái)。至于上述他(tā)的(de)著名之“四句教”,簡直與禅宗六祖惠能教人(rén)的(de)“無邊衆生誓願度,無盡煩惱誓願斷,無量法門誓願學,無上佛道誓願成”完全相似。又如他(tā)在《正蒙》中所稱的(de)“大(dà)心”,便是直接套用(yòng)佛學“大(dà)心菩薩”的(de)名詞和(hé)涵義,而加以儒家化(huà)的(de)面貌而已。也(yě)可(kě)以說,他(tā)是因襲禅宗六祖的(de)思想而來(lái)的(de)異曲同工,也(yě)并不爲過。關于張橫渠所著的(de)《正蒙》,以及他(tā)的(de)“理(lǐ)氣二元”的(de)立論,則大(dà)半是挹取道家的(de)思想,啓發易理(lǐ)觀念,這(zhè)也(yě)是事實。這(zhè)些都是從他(tā)“初求之佛、老”而得(de)來(lái)的(de)啓迪,大(dà)可(kě)不必有所諱言。
(五)二程的(de)思想與禅佛
二程——兄颢(明(míng)道先生)、弟(dì)頤(伊川先生)“少時(shí),從學于周濂溪,慨然有求道之志,後泛濫諸家,出入老、釋幾十年,返求諸六經而後得(de)之雲”。根據《宋史》記載這(zhè)些有關的(de)資料,宋儒的(de)理(lǐ)學大(dà)家們,幾乎都是先有求道之志,而且都是先求之于佛、老若幹年或幾十年後,再返求諸六經或孔、孟之說而得(de)道的(de)體用(yòng)。我們都知道,六經與孔、孟之書(shū),至今猶在。佛、道之書(shū),也(yě)至今猶在。大(dà)家也(yě)都讀過這(zhè)些書(shū),究竟是六經與孔、孟之書(shū)易讀,抑或是佛、道之書(shū)難讀,這(zhè)是不須再多(duō)辯說的(de)問題。同時(shí)佛、老之“道”,其“道”是什(shén)麽?六經、孔孟之書(shū),其“道”又是什(shén)麽?這(zhè)個(gè)問題,界限也(yě)極其分(fēn)明(míng)。真不明(míng)白何以他(tā)們都願意把這(zhè)些問題,混作一談,便說“‘道’在是矣”的(de)含糊話(huà),這(zhè)未免使“理(lǐ)學”的(de)聲光(guāng),反而大(dà)爲減色。至于二程之學,如較之周、張、邵子,則在氣度見地上,早已遜有多(duō)籌了(le)。
《宋史·道學傳》說大(dà)程子“出入老釋幾十年”,其弟(dì)伊川也(yě)如此說他(tā)。但明(míng)道的(de)辟佛與非禅之語有說:“山河(hé)大(dà)地之說與我無關,要簡易明(míng)白易行。”這(zhè)是他(tā)批評《楞嚴經》的(de)話(huà)。如用(yòng)現代眼光(guāng)來(lái)看,簡直是毫無科學頭腦(nǎo),非常颟顸。因此可(kě)以說他(tā)的(de)“理(lǐ)學”思想,也(yě)隻屬于“心理(lǐ)道德”的(de)修養學說,或者是“倫理(lǐ)”的(de)養成思想而已。又如他(tā)批評《華嚴經》的(de)“光(guāng)明(míng)變相,隻是聖人(rén)一心之光(guāng)明(míng)”,未免太過儱侗,不知此語已自落入禅家機鋒轉語的(de)弊病,并非真知灼見。又如批評《涅槃經》要旨“一切衆生皆有佛性”的(de)話(huà),他(tā)便說:“蠢動含靈,皆有佛性爲非是。”更是缺乏哲學思辨主題的(de)方法。餘如說:“道之不明(míng),異端害之也(yě)。昔之害近而易知,今之害深而難見。昔之惑人(rén)也(yě),乘其暗迷;今之惑人(rén)也(yě),由其高(gāo)明(míng)。與雲窮神知化(huà),而不足開物(wù)成務;其言無不同偏,實外于倫理(lǐ),窮深極微而不入堯舜之道。”這(zhè)些都是似是而非、隔靴搔癢的(de)外行話(huà)。佛道與儒家的(de)堯舜思想,本來(lái)就是兩回事,不必混爲一談,多(duō)此一辟。而且佛學中再三贊揚治世的(de)“轉輪聖王的(de)功德,等同如來(lái)”的(de)福業,也(yě)并不專以出世爲重而完全忽略入世的(de)“倫理(lǐ)”思想。所謂“轉輪聖王”,便有近似儒家所謂“先王之道”的(de)情況。況且佛學大(dà)乘的(de)菩提心戒,對(duì)于濟人(rén)利物(wù)救世的(de)思想,尤有勝于儒家的(de)積極,他(tā)都忽略不知,也(yě)甚可(kě)惜。至于他(tā)批評禅的(de)方法說:“唯覺之理(lǐ),雖有敬以直内,然無義以方外,故流于枯槁或肆恣。”這(zhè)倒切中南(nán)宋以後禅家提倡參究(參話(huà)頭、參公案等)的(de)方法,以及重視機鋒、轉語等便認爲是禅宗的(de)真谛之流弊,的(de)确有其見地。但他(tā)對(duì)于真正的(de)“禅”是什(shén)麽?老實說,畢竟外行,有太多(duō)的(de)觀念尚待商榷。
程伊川與佛教的(de)禅師們,也(yě)常相往來(lái),宋人(rén)編的(de)《禅林(lín)寶訓》中,便有靈源禅師給程伊川的(de)三封信,其中有“聞公留心此道甚久”、“天下(xià)大(dà)宗匠(jiàng)曆叩殆遍”、“則山僧與居士相見,其來(lái)久矣”、“縱使相見,豈通(tōng)唱和(hé)”、“雖未接英姿,而心契同風”等語。伊川也(yě)曾見過靈源之師晦堂禅師,故靈源有信給他(tā)說:“頃聞老師言公見處,然老師與公相見時(shí),已自傷慈,隻欲當處和(hé)平,不肯深挑痛劇”等語。而且還(hái)有别的(de)資料,足可(kě)證明(míng)伊川與靈源禅師等的(de)通(tōng)問交往,雖老而未斷。這(zhè)等于朱熹要鑽研道家的(de)丹道之學,爲了(le)一個(gè)門戶之見的(de)憍慢(màn)心所障礙,不肯問道于白玉蟾,到老也(yě)沒有一點入處,隻好化(huà)名崆峒道士鄒䜣,注述《參同契》一書(shū)以自慰了(le)。《二程遺書(shū)》又說:“伊川少時(shí)多(duō)與禅客語,以觀其學之淺深。後來(lái)則不睹其面,更不詢問。”但他(tā)嘗說:“隻是一個(gè)不動之心,釋氏平生隻學得(de)這(zhè)一個(gè)字。”“學者之先務在固心志。其患紛亂時(shí),宜坐(zuò)禅入定。”這(zhè)與以“靜”爲學的(de)基礎一樣,同樣地都以采用(yòng)禅定(并非禅宗)爲教學的(de)方法。然而他(tā)的(de)排佛言論卻特别多(duō),嘗自言:“一生正敬,不曾看莊列佛書(shū)。”如果真的(de)如此,則未免爲門戶的(de)主觀成見太深,自陷于“寡聞”的(de)錯誤。因此他(tā)引用(yòng)佛學,便有大(dà)錯特錯之處,例如說:“釋氏有理(lǐ)障之說,此把理(lǐ)字看錯了(le)。天下(xià)唯有一個(gè)的(de)理(lǐ),若以理(lǐ)爲障,不免以理(lǐ)與自己分(fēn)爲二。”他(tā)對(duì)于佛學“理(lǐ)障”(即所知障)的(de)誤會,外行如此,豈能服天下(xià)知識佛學者之心。并且又不知辨析的(de)方法,不知比較研究的(de)真實性,但在文字名詞上與佛學硬争,更落在專憑意氣之争的(de)味道了(le)。陸象山所謂“智者之蔽,在于意見”,真可(kě)爲伊川此等處下(xià)一注腳。
至于他(tā)教學者的(de)方法說:“涵養須用(yòng)敬,進學則在緻知。”在“用(yòng)敬”之前,又須先習(xí)“靜坐(zuò)”。他(tā)所講的(de)“靜坐(zuò)”、“用(yòng)敬”、“緻知”的(de)三步工夫,正是由佛學“戒、定、慧”三學的(de)啓迪變化(huà)而來(lái),但又并不承認自己受其影(yǐng)響,且多(duō)作外行語以排佛,反而顯見其失。實例太多(duō),不及枚舉,暫時(shí)到此爲止。其他(tā)如程明(míng)道先生的(de)名著《定性書(shū)》文中說“動亦定,靜亦定,無将迎,無内外……既以内外爲二本,則又烏可(kě)遽語定哉”等觀念,完全從他(tā)出入佛、老,取用(yòng)《楞嚴經》中楞嚴大(dà)定的(de)迥絕内外中間之理(lǐ),而任運于“妙湛總持”的(de)觀念作基礎,再加集莊子的(de)“心齋”等思想而來(lái)。但對(duì)于理(lǐ)學家們的(de)教學修養的(de)價值,那真是不可(kě)輕易抹煞的(de)偉著。
我們略一引述宋儒理(lǐ)學家的(de)五大(dà)儒與禅之關系的(de)簡要處以外,其餘諸儒中,有關這(zhè)些資料者,多(duō)得(de)不及縷述,隻好到此暫停了(le)。
(六)有關理(lǐ)學家們排佛的(de)幾個(gè)觀念
根據以上所講,好像在說宋儒的(de)理(lǐ)學,都是因襲佛、道兩家學術思想的(de)變相,理(lǐ)學的(de)本身,便無獨特的(de)價值似的(de)。這(zhè)是不可(kě)誤解的(de)事,須要在此特作聲明(míng)。現在隻因時(shí)間與篇幅的(de)關系,僅就本題有關禅與理(lǐ)學的(de)扼要之處,稍作簡介而已。如果必須要下(xià)一斷語,我們便可(kě)以說:“禅宗到南(nán)北(běi)宋時(shí),已逐漸走向下(xià)坡,繼起而王于中國學術思想界者,便是‘理(lǐ)學’。相反地,元、明(míng)以後一般的(de)禅宗,或多(duō)或少已經滲有‘理(lǐ)學’的(de)成分(fēn)了(le)。”換言之,理(lǐ)學就是宋代新興的(de)“儒家之禅學”。元、明(míng)以後的(de)禅宗,也(yě)已等同是“禅宗之理(lǐ)學”了(le)。佛學不來(lái)中國,隋、唐之間佛教的(de)禅宗如不興起,那麽,儒家思想與孔、孟的(de)“微言大(dà)義”可(kě)能永遠(yuǎn)停留在經疏注解之間,便不會有如宋、明(míng)以來(lái)儒家哲學體系的(de)建立和(hé)發揚光(guāng)大(dà)的(de)局面。幸好因禅注儒,才能促成宋儒理(lǐ)學的(de)光(guāng)彩。
如果再要追溯它的(de)遠(yuǎn)因,問題更不簡單。自漢末佛教傳入中國以來(lái),引起學術思想界儒、佛、道三家的(de)同異之争,一直曆魏、晉、南(nán)北(běi)朝而到隋、唐,争論始終不已。由漢末牟融著《理(lǐ)惑論》,調和(hé)三教異同之說開始,直到唐代高(gāo)僧道宣法師彙集的(de)《廣弘明(míng)集》爲止,其中所有的(de)文獻資料,随處可(kě)見在中國的(de)學術思想界中,始終存在著(zhe)這(zhè)股洪流。初唐開國以後,同尊三教,各自互擅勝場(chǎng),已經漸入融會互注的(de)情況。宋儒理(lǐ)學的(de)興起,本可(kě)結束這(zhè)個(gè)将近千年來(lái)的(de)争議(yì),但畢竟在知識見解的(de)争論上,更有甚于世俗的(de)固執。理(lǐ)學家們仍然存有許多(duō)不必要的(de)意見與誤解,因此而使禅與理(lǐ)學,都不能爆放更大(dà)的(de)慧光(guāng),這(zhè)是非常遺憾的(de)事。
但在禅宗方面,卻一直對(duì)儒家思想和(hé)理(lǐ)學,并無攻毀之處,甚之,還(hái)保持相當的(de)尊重。因爲無論學禅學佛的(de)人(rén),隻要是讀過書(shū)的(de)人(rén),都曾受過孔、孟思想教育熏陶,不會忘本而不認賬。即使毫未受過教育的(de)學佛者,凡是中國人(rén),對(duì)于聖人(rén)孔、孟思想的(de)尊敬,也(yě)都牢入人(rén)心。并且已将儒家和(hé)孔、孟的(de)思想,變成個(gè)人(rén)生活與中國社會形态的(de)中心,極少輕蔑的(de)意識。
理(lǐ)學家們排佛的(de)要點,除了(le)對(duì)于“宇宙觀”和(hé)形而上“本體論”的(de)争辯以外,攻擊最力的(de),便是出世(出家)和(hé)入世(用(yòng)世)的(de)問題。有關“宇宙觀”和(hé)形而上“本體論”的(de)哲學思辨,理(lǐ)學家們的(de)觀點,雖然屬出入佛、老而契入《易經》與孔、孟的(de)學術思想範圍,畢竟還(hái)不如禅佛的(de)高(gāo)深。此事說來(lái)話(huà)長(cháng),而且也(yě)太過專門,暫時(shí)不談。至于有關入世和(hé)出世的(de)問題,的(de)确有值得(de)商榷之處。不過他(tā)們忘記了(le)在唐、宋以來(lái)的(de)中國社會,雖有大(dà)同仁義的(de)思想,但并未像現代有社會福利的(de)制度,因此貧富苦樂(yuè)懸殊,以及鳏、寡、孤、獨、殘疾、疲癃、幼無所養、老無所歸的(de)現象,也(yě)是一件非常嚴重的(de)社會問題。幸好有了(le)佛、道兩教出家人(rén)可(kě)以常住寺觀等的(de)制度存在,無形之中,已爲過去曆代帝王治權和(hé)社會上,消弭一部分(fēn)的(de)禍亂,解決了(le)許多(duō)不必要的(de)慘痛事故,未嘗不是一件極大(dà)的(de)功德。因此而批評離世出家,就等同墨子“無父無君”的(de)思想,那也(yě)是一般不深入的(de)看法。這(zhè)是理(lǐ)學家們,大(dà)多(duō)都未深入研究大(dà)乘佛學的(de)精神和(hé)大(dà)乘戒律思想的(de)誤解。況且墨子思想的(de)“尚同”、“兼愛(ài)”、“尚賢”,也(yě)并非真如他(tā)們所說的(de)完全是“無父無君”的(de)慘酷。不過這(zhè)又要涉及儒、墨思想的(de)争端問題,在此不多(duō)作牽連了(le)。
此外,宋、明(míng)以來(lái)理(lǐ)學家們講學的(de)“書(shū)院”規約之精神,是受禅宗“叢林(lín)制度”以及《百丈清規》的(de)影(yǐng)響而來(lái)。理(lǐ)學家們講學的(de)“語錄”、“學案”,完全是套用(yòng)禅宗的(de)“語錄”、“公案”的(de)形式與名稱。不過這(zhè)些都是屬于理(lǐ)學與禅宗有關的(de)小事,順便一提,聊供參考而已,并不關系大(dà)節。
總之,本題是有關中國學術思想史的(de)演變與發展的(de)大(dà)問題,實非匆促可(kě)以討(tǎo)論的(de)事。當時(shí)因爲黃(huáng)得(de)時(shí)、錢鞮男(nán)兩位先生的(de)命題,我隻好提出一些有關的(de)簡略報告,等于是作一次應考的(de)繳卷,并未能夠詳盡其詞,敬請見諒。
(西元一九七二年,台北(běi)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