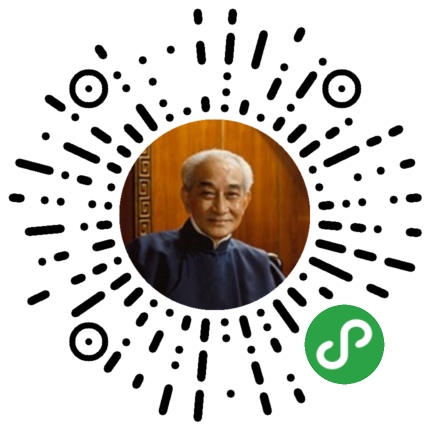南(nán)師文選
南(nán)懷瑾先生:廿世紀前六十年來(lái)教育的(de)變和(hé)惑
教育乃國家命脈和(hé)民族精神之所系。我們的(de)教育,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來(lái),從舊(jiù)式的(de)傳統,幾經變革而到現在(編按:本書(shū)初版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)。但是我們還(hái)得(de)承認我們現在的(de)教育思想與教育制度,雖然形似進步,仍然存有太多(duō)的(de)困擾與矛盾。因此促使青少年們在現行的(de)教育方式之下(xià),産生了(le)許多(duō)心理(lǐ)的(de)反抗與思想的(de)迷惘。有關這(zhè)個(gè)問題,我們必須要從新舊(jiù)教育的(de)實際變相中尋求前因和(hé)後果,才能知所先後,深思反省而莊敬自強起來(lái);否則,又會本末倒置,變成一個(gè)“不知所雲”的(de)結論。
由舊(jiù)式的(de)家塾到新式的(de)學校
我們的(de)傳統,遵照(zhào)《禮記》的(de)精神,童子六歲入小學,每個(gè)人(rén)到了(le)六歲,便應該開始讀書(shū)識字,但是在過去農業社會的(de)鄉村(cūn)或城(chéng)市中,國民經濟與風俗習(xí)慣并不能做(zuò)到人(rén)人(rén)都在六歲的(de)時(shí)候便可(kě)讀書(shū)受教育。第一,并無公家設立的(de)學校,全靠大(dà)家湊足人(rén)數和(hé)财力,專請一位老師設立一個(gè)“蒙館”——等于現在的(de)小學和(hé)幼稚園的(de)家塾,真不容易辦。第二,一般鄉村(cūn)情形,并不都像孟子說的(de)“五畝之宅,樹之以桑,五十者可(kě)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,無失其時(shí),七十者可(kě)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,勿奪其時(shí),八口之家,可(kě)以無饑矣。謹庠序之教,申之以孝悌之義,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”。事實上,卻是“加之以師旅,因之以饑馑”、“老弱轉乎溝壑,壯者散而之四方”。這(zhè)便是清朝末代的(de)大(dà)體現象。所以農村(cūn)子弟(dì)即便比較生活安定的(de),也(yě)大(dà)都是“兒(ér)童未解供耕織,也(yě)旁桑陰學種瓜”。讀書(shū)、考功名、做(zuò)官,那是某一些人(rén)專有的(de)職業,一般人(rén)們好像本來(lái)就不存非分(fēn)之想似的(de)。
如果有了(le)适當的(de)家塾,一個(gè)子弟(dì)開始進入學館去“啓蒙”求學時(shí),那真如辦一件相當慎重的(de)大(dà)事似的(de)。當然那時(shí)隻限于男(nán)孩而言,女(nǚ)性受教育的(de)機會少之又少,可(kě)以說是絕無僅有的(de)事。稍能注重子弟(dì)入學的(de)家庭,在開始上學的(de)一天,便先要他(tā)跪拜了(le)祖宗的(de)靈位,背著(zhe)書(shū)包,由大(dà)人(rén)陪送他(tā)去入學。到了(le)學塾裏,先要跪拜大(dà)成至聖先師孔子的(de)聖像或神位,然後再拜老師。安好桌位,才由老師慢(màn)慢(màn)地開始教授讀書(shū)和(hé)寫字。距今三十年前(編按:本書(shū)初版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),我們對(duì)于老師,都是尊稱爲“先生”,或者在先生之上,加上一個(gè)姓氏。至少,我是從來(lái)沒有聽(tīng)到過稱教學的(de)“先生”叫老師的(de)。一般學生抑或學手工藝的(de)學徒,都稱老師叫“師傅”。隻有民間社會,對(duì)一般工匠(jiàng)叫“老司”或“老師”。我所知道在江南(nán)一帶,大(dà)緻相同。現在時(shí)代的(de)風氣變了(le),在這(zhè)二三十年來(lái),叫“老師”做(zuò)“先生”的(de),卻被認爲是不禮貌。由此可(kě)知是非禮義的(de)标準,完全是因時(shí)因地的(de)人(rén)爲而定,哪裏會有一成不變的(de)絕對(duì)規範呢(ne)?
舊(jiù)式家塾的(de)讀書(shū)
舊(jiù)式家塾裏對(duì)寫字的(de)啓蒙
講到啓蒙時(shí)期的(de)寫字,更爲有趣。起初開始練習(xí)寫字,便要描紅。那是在一張白紙上印好紅字,用(yòng)毛筆蘸墨去填寫。一個(gè)六七歲的(de)小學生,連拿毛筆是怎樣的(de)拿都不清楚,馬上就要描紅寫字,真也(yě)是件不容易的(de)事。于是老師和(hé)大(dà)人(rén)們,往往便爲你“把筆”練習(xí)(用(yòng)自己的(de)手握在學生的(de)手上,幫他(tā)寫字),那時(shí)開始描紅的(de)紙上,所寫的(de)紅字并不太好,但是卻是具有傳統文化(huà)的(de)曆史權威的(de)一首詞句,從宋代開始,便一直爲啓蒙入學時(shí)期的(de)小學生們所應用(yòng),它的(de)内容是:“上大(dà)人(rén),孔乙己。化(huà)三千,七十士。爾小生,八九子。佳作仁,可(kě)知禮也(yě)。”這(zhè)首意義似通(tōng)非通(tōng)的(de)詞句,将近千年以來(lái),應用(yòng)得(de)非常廣泛。距今四十年前,我碰到一位學道術的(de)人(rén),他(tā)會畫(huà)符念咒,大(dà)家都說他(tā)神通(tōng)廣大(dà),法術無邊。後來(lái)我和(hé)他(tā)接近以後,才知道他(tā)出賣的(de)風雲雷雨(yǔ),完全靠一個(gè)很有效驗的(de)咒子。你說那是什(shén)麽咒呢(ne)?原來(lái)他(tā)反複所念的(de),便是這(zhè)首《上大(dà)人(rén)》。另有一派專門替人(rén)畫(huà)符念咒治病的(de)術士,他(tā)們口中念念有詞的(de),便是“大(dà)學之道,在明(míng)明(míng)德”的(de)首一章(zhāng),你說可(kě)笑(xiào)不可(kě)笑(xiào)。
學寫字,先描紅,還(hái)不錯。有的(de)窮苦學生,連描紅的(de)《上大(dà)人(rén)》也(yě)買不起,隻用(yòng)一塊木(mù)闆,漆成黑(hēi)白兩面,用(yòng)毛筆蘸墨在白色的(de)一面上學寫字。等到老師看不見時(shí),便用(yòng)一堆墨倒在白闆上,用(yòng)嘴吹它一口氣,再來(lái)用(yòng)指頭東抹西畫(huà)一番,便會變出一幅很有趣的(de)畫(huà)面,山水(shuǐ)人(rén)物(wù)、蟲魚花鳥都有。所以我常常想到當時(shí)那些小同學的(de)影(yǐng)像畫(huà),真夠先進,也(yě)真夠“抽象”,如果拿到現在來(lái),一定是最時(shí)髦的(de)作品。但是我們當時(shí)在家塾裏的(de)同學們,卻并不時(shí)髦,因爲大(dà)家書(shū)包裏都帶著(zhe)毛筆、墨、硯台和(hé)書(shū)本,在家塾裏讀了(le)一天的(de)書(shū),東畫(huà)西畫(huà),每個(gè)人(rén)的(de)手上、臉上、嘴上,都塗抹得(de)一塌糊塗,都自勾成一個(gè)像京戲裏醜角的(de)面孔。
講到家塾,我們顧名思義,一定都設在某一個(gè)人(rén)的(de)家裏喽?其實,并不盡然,除了(le)殷實的(de)富戶人(rén)家,或者世代書(shū)香之後,可(kě)以有空房(fáng)子專門設立家塾,供子弟(dì)們讀書(shū)以外,大(dà)多(duō)數的(de)農村(cūn)社會,都做(zuò)不到有這(zhè)樣好的(de)教育環境。所以多(duō)數的(de)家塾設立在某某宗祠的(de)祠堂或寺廟裏。因爲這(zhè)些地方比較清靜寬廣,學生們還(hái)有活動的(de)餘地,蕩秋千、踢毽子、疊羅漢、打小小的(de)群架,那也(yě)是常有的(de)事。但在偏僻地方的(de)三家村(cūn)裏的(de)家塾,情形又當别論。在此,我要聲明(míng),爲什(shén)麽一直要稱它做(zuò)家塾,卻不用(yòng)私塾的(de)名稱呢(ne)?因爲私塾是在民國成立以後,建立了(le)新的(de)教育制度,對(duì)于過去私家設立的(de)家塾,依法稱它爲私塾。事實上,在六十年前後的(de)家塾,并無所謂公立或私立的(de)嚴格差别。
至于在家塾裏教書(shū)的(de)老師,說來(lái)真有無限的(de)感慨。同時(shí),也(yě)可(kě)因此而爲古今中外從事教學的(de)先生們同下(xià)一掬傷心而凄涼的(de)淚水(shuǐ)。大(dà)概我們都知道過去私家教學的(de)風格和(hé)習(xí)慣,凡是講到家裏教書(shū)先生的(de)代名詞,叫做(zuò)“西席”。老師們稱呼主人(rén)的(de)雅号,叫做(zuò)“東主”或“東翁”。除了(le)一般已經有了(le)初步功名成就的(de)子弟(dì),再請一位有學問或有功名的(de)“西席”先生來(lái)家專門教讀以外,其他(tā)一般家塾所請的(de)老師,不是落第的(de)書(shū)生,便是窮而無奈的(de)酸丁。表面上雖然表示尊敬,實際上,并不受一般社會所重視。他(tā)們生活的(de)刻苦,以及報酬待遇的(de)菲薄,真是不堪想象。那時(shí),并非以月(yuè)薪計算(suàn)報酬,隻是以年節計算(suàn)實物(wù),或者加上當時(shí)極其少數的(de)貨币(銀兩或銀洋),一年辛苦所得(de),也(yě)僅得(de)溫飽而已。至于以此養家活口,那就苦不堪言了(le)。所謂“命薄不如趁早死,家貧無奈做(zuò)先生”的(de)感慨,都是這(zhè)種情況中所産生的(de)悲哀。可(kě)是話(huà)說回來(lái),碰到有些“冬烘”迂腐的(de)學究,實在也(yě)會使人(rén)覺得(de)“百無一用(yòng)是書(shū)生”的(de)可(kě)厭。凡事總有正反不同的(de)兩面道理(lǐ),當然不能一概而論。但大(dà)體說來(lái),當時(shí)多(duō)數的(de)教書(shū)先生們,一言以蔽之,都在清苦中度過他(tā)的(de)一生。清代的(de)名士鄭闆橋(燮),在沒有考取功名以前,也(yě)曾經做(zuò)過教書(shū)先生,他(tā)便寫過一首足爲千秋後世同聲一歎的(de)名詩,如雲:
教讀原來(lái)是下(xià)流,
半饑半飽清閑客,
課少父兄嫌懶惰,
而今幸作青雲客,
傍人(rén)門戶過春秋。
無鎖無枷自在囚。
功多(duō)子弟(dì)結冤仇。
遮卻當年一半羞。
又相傳光(guāng)緒時(shí),有李森廬者,以教讀爲業,某年歲除,不能歸,作詩寄其妻雲:“今年館事太清平,新舊(jiù)生徒隻數人(rén)。寄語賢妻休盼望,想錢還(hái)賬莫勞神。”“我命從來(lái)實可(kě)憐,一雙赤手硯爲田。今年恰似逢幹旱,隻半收成莫怨天。”
現在教書(shū)先生的(de)情形,雖然沒有完全像這(zhè)樣的(de)慘痛,但是以“舌耕”爲務的(de)人(rén),比較一般從事有關工商職業的(de),在物(wù)質生活的(de)享樂(yuè)上,到底還(hái)有很大(dà)的(de)差距。過去是“一席青氈”,罰坐(zuò)在冷(lěng)闆凳上。現在是一張聘約,罰站在冷(lěng)櫃台。況且一校一系一派,無形中各自形成圈圈,清儒童二樹所謂:“左圈右圈圈不了(le),不知圈了(le)有多(duō)少?而今跳出圈圈外,恐被圈圈圈到老。”古今中外,同此一例,這(zhè)也(yě)正是人(rén)類思想和(hé)心理(lǐ)的(de)一個(gè)重大(dà)問題。